金石学研究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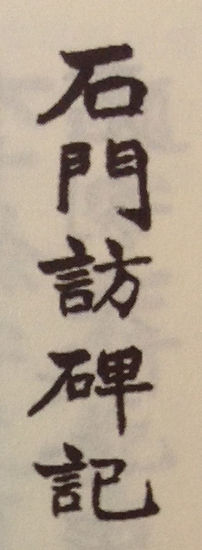 吴大澂所书“石门访碑记”
吴大澂所书“石门访碑记”
两宋以来,所有治学严谨的金石学家均经历过踏勘考察、募工拓制及案头考订、鉴藏这几道必由之路。同时,鉴于金石学载体以传拓印刷品形式出现,随着不同版本拓片,促进并加强了各地无缘经历访碑、椎拓这几重学术境界。继上期刊发两宋和清代中叶的金石学研究后,本期将以晚晴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关系研究为线索, 追忆历史上的金石前缘。
陶喻之
(接上期)晚清宦游汉南尤其亲历交通闭塞,不在蜀道干线陇南西狭访碑的金石学大家,是继王森文后一个甲子的陕甘学政吴大澂。据《恒轩日记》自述1870年他已随湖广总督李鸿章幕西行入陕;而《吴愙斋自订年谱》载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一正式受任,九月十三日,雅好金石的他以手绘古器图请同时学人李慈铭题诗为其视学秦陇壮行。李有“当代论金石,潘(祖荫)陈(介祺)古癖推。翰林谁继起,吾子擅清才”和“百二秦关启,山河接陇凉。此邦多古迹,余事及缣缃”之咏。与此同时,陈介祺致函古币专家鲍康艳羡:闻清卿兄视学陕甘,可喜之至,好古而即得游古地,真为有福。又曰:“张孝达(之洞)留视蜀学,当亦可得金石,与清卿各树一帜矣。”光绪十年(1884)署名“笏盫”者题识被誉为“甲骨之父”山东福山金石学家王懿荣《天壤阁杂记》也说:“今时谈金石者,首推潍县陈学士介祺,次则吾家少保公张香涛制军之洞。若吴丈清卿,王君廉生两家,亦广收博采。地不爱宝,日出不穷,较阮相国、吴子苾、刘燕廷当时增之十倍。”值得注意的是,同治末年既是以陈介祺为首金石学家学谊渐趋活跃的重要时间结点, 且涉及蜀道访碑、椎拓与鉴藏等金石学活动,也恰好围绕陈、吴、王诸人展开。其中吴因公按试秦陇,王则以私于光绪四年入蜀省亲;虽王亦无暇造访石门摩崖,但犹留心一路古物,《天壤阁杂记》遂有“过褒城,见一路古砖在人家墙上,不得取”,“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等载。
就陈函请吴访碑、委托椎拓并寄交王代为转达等金石学互动情况掌握,学术界主要借重其交往半世纪后出版《簠斋尺牍》、《吴愙斋尺牍》等予考察,而三人当年亦凭借对彼此声誉、信誉的了解,完全依靠书信切磋学问,并未当面促膝请益;像陈、王仅有一面之缘,而陈、吴缘悭分浅,终陈一生,碌碌宦游各地的吴竟从未跟闲居齐鲁通信密切的金石学领袖相谋面。至于作为晚辈后学的王、吴结交当时久负盛名的陈而与之频通尺牍缘起,均始于同治十二年与陈书信热络的鲍康和潘祖荫引荐。于是,就在吴上任后四日,陈即递送手札感谢吴托鲍转赠其长孙婚礼贺联,又赞“久于伯寅少农(金石学家潘祖荫)书中得闻风雅,复于攀古楼款识刻得读大著,已深向往”,并称于鲍函“欣闻荣膺新命,视学三秦”,表达了希望成为金石契友而互通有无心愿,所谓“惟乞古缘所遇,不忘远人。羡有奇之必搜,企有副之必惠,当悉拓敝藏以报也”,最后话锋一转,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石门颂》诸汉刻,均望洗剔,以绵料厚纸先扑墨后拭墨精拓之,水用芨胶去矾。拓费必当即缴,切勿从赐。收拓必详其目,免有遗复。”而陈、王往来也始于同年馈赠金石拓片,直至光绪十年几每函必伴拓片。 正是基于三人同好书法古文字的金石之缘,终于促成其为“三颂”访碑、椎拓而合作的三角关系。
至于陈之所以关注“三颂”等汉魏蜀道摩崖,似乎跟他受前辈金石学家刘喜海、何绍基就此倾注大量精力鉴藏、摹写等影响有关。前已论及,同治十一年秋,陈已寄《石门颂》托吴云请何题诗,说明弆藏并不迟于何、刘;而刘无论家族背景、人际关系还是鉴藏、治学精神, 尤其搜集蜀中石刻拓本兴趣,同样让他印象深刻而挥之不去。此时适值宦游三秦之吴投联问路,自然正中陈怀,遂拟乘此了却夙愿,因有相互两年多直接或经王间接转达、寄交石刻拓片的金石学通信。以下着重提炼其间重要研究信息加以探讨。
吴大澂同治十三年重阳“按临汉中试事,碌碌四十余日,疲精耗神,与京华故人音问疏阔。”深感“僻处秦中,无可与语。京华故人,惟王廉生农部邃于金石之学,相契最深,别后数月曾未得其手书;孝达入蜀懒于作札,偶有所见无可质证。倘蒙不弃,时惠尺书,以慰岑寂,片楮之赐,珍逾拱璧,欣幸何如。关中自兵燹以后,寒士荒经,文风久已不振,輶车所及,与诸生苦口劝勉,有善必奖,有弊必惩,冀于士风稍有裨益。所愧根底浅薄,不足为士林表率,时滋惶悚。山林隐逸之士,讲求正学者,当有数人。近今俗当以时艺相衔,敦本励行,目为迂儒,不得不稍示激扬,以为通经明理者劝”,幸到汉中遇两位金石学知音——褒城教谕罗秀书和椎拓技师张懋功,始解其谈艺寂寥,且对此行完成陈介祺嘱托亦良多帮助。
关中罗秀书同治十年前后宦游汉中即与同道数至石门,“剥苔封,洗尘泥,历数月始将模糊之字考证明确,岩石间仿佛有字者,皆搜括而出之,因录集一册,以便携览。” 因慕吴大澂金石学盛名,遂于其来汉试毕“遣舟来迎” 赴石门访碑遂其宿愿。据罗透露:“甲戌冬,吴学宪将文(《李君表》)理考全,拟翻刻一石未果”。但此行吴对罗于此乱世之秋犹沉浸于金石之学已刮目相看,故当罗旋呈其考镜褒谷全境而较之《石门碑释》更见周全研究专著《褒谷古迹辑略》,吴欣然命笔题签并署“同治甲戌孟冬吴大澂观于汉南试院”以示褒奖。而石门拓工张懋功似乎也由罗荐于吴遂成其在陕南、陇南按陈介祺函授精拓摩崖刻石的专职技师。因据咸丰八年罗撰隶书《汉忠武侯诸葛公八阵图注说》碑载:“张子懋功,性嗜古,问阵图说,故书此。”表明罗、张在吴来汉前已结识并过从甚密。另据光绪八年潘矩墉《游石门记》碑载:“邑人张茂功,精音律,能毡腊,善与人交。家在石门对岸,茅屋数椽,树木周匝,殊觉幽雅。约往少憩,具鸡黍饷客,更出琵琶而侑酒,虽非流水高山,然亦足以移情矣。” 由此可见张并非悟性全无等闲之辈,而是勤学善思有头脑的能工巧匠。
而由陈、吴通信可知陈对石刻拓本精度近乎求全责备,特别就以往拓工不屑碑额需求极大,如嘱“若古石则须厚棉纸先扑后拭不妨墨重,方见笔画。……栈道日下其上颇有汉刻,近蜀处可访之,并可语孝达学使也”,“《褒斜开》后一行、《惠安西表》四字额、《五瑞图》小字一行,乞勿遗,《耿勋》亦乞精拓。”再如“《石门》额乞早寄此间”,“《石门颂》、《西狭颂》多求精拓五六份,额皆倍之,切切乞乞。”但当年陕西椎拓技术普遍低劣,为此,吴致陈函多次提及“秦中刷手甚劣”,“此间拓手多自以为是,又不耐烦,以速为贵。教以先扑墨后拭墨之法多不听从。幕友家人中,亦能拓而不能精。汉中如有良工,当令精拓石门诸刻。安得瑯瑘拓手遍拓三秦碑碣耶?”“此间拓手之不精,即此可见《唐公房》碑阴尚有数十字,嘱其一并椎拓,仅拓得一份,其意以为寥寥数行,殊不愿拓,亦属可笑。”而罗荐张匠经吴点拨、栽培、演示和监拓却颇能入陈门径,故深得吴所倚重,遂于“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一路逆水行舟、跋涉登攀进褒谷甚至夜宿张家,观风雪满山,听“江声如吼,终夕潺潺不绝”。次日由罗、张等陪同“游石门,风雪中攀萝附葛,访得永寿刻石数行及《君开通褒斜》刻石尾段残字,亦一快事,惟嘱打碑人先拓数纸”,此“打碑人”即后受吴全权委托遍拓陕南、陇南重要摩崖而谊称莫逆之张懋功,故其姓名迭见吴致陈函如“成县距褒城七百里,《西狭颂》、《五瑞图》、《耿勋碑》均遣石门张懋功于明春二三月间往拓……《西狭颂》有二刻,天井摩崖想亦不致剥蚀……明年当嘱张懋功就近访之,未识有此奇缘否?”“明年当遣张懋功拓之,必可稍精。褒城距城固不远,略阳《郙阁颂》,亦当遣拓。石门工价向不甚昂,给以倍价,尚听指挥……”“艰登陟为劳,遂以舁石事属张懋功,不及手自摩挲……”“顷由褒城寄到石门汉魏诸刻,纸墨之精,万不如尊处,拓工较寻常帖估所货,略有一二可取……李苞题名残字两行刻在石门洞外高崖处,下临深涧,游者须至崖畔极险处仄足而立仰视方见。拓工于洞内立架施一长板用绳捆身转面向里,方可上纸,故仅拓数本……潘、韩题字亦竟无获,访碑之不易如此。拓工已赴成县,《西狭》、《耿勋》,须秋初方到手……”“拓工自成县回,携到《西狭》、《耿勋》并略阳《郙阁颂》,较胜常拓。《西狭》有额并有下段题名三行,《耿勋》额甚高,不易拓,石有流泉,纸湿难干,各寄一本奉呈赏鉴。”陈得吴撰《石门访碑记》暨其称张拓制技术了得起初疑信参半,故回函:“读书及《访碑记》,如身历石门,唯无好拓手,仍似辜负此游耳。”及得吴寄张拓,始对拓片质量表示认可并提出更严格要求:“张茂功拓墨已异俗工,未知是先扑后拭否,拓不到则多不可见,拓过重则可见者又有微茫处,参之则可精到。《石门颂》尚欲再精拓一二纸并额四五纸;《杨淮表》表字上似宜有字,何不多拓数寸,其拓似初上墨时太干。”“闻得访石门诸刻,务并额及汉时题字记精拓之,额尤须多拓,拓者细心解事,当不减秦石之有新获也。”
众所周知,吴氏治学本侧重案头研究三代彝器,自称“于汉隶源流,茫无所知”。经历此番跋山涉水访碑暨与陈介祺尺牍往还,对汉魏摩崖石刻研究甚至拓制技艺均有长进,这从《石门访碑记》后长篇考稽文字足见一斑。他既亲临石门石刻群更是绝无仅有涉足西狭谷地考察沿途汉代摩崖的晚近重要金石学家; 而张懋功乃陈、吴金石学思想的忠实、具体执行与实践者,陈、吴及其朋侪所获“汉三颂”等相关石刻拓本就均出其手,故后吴替张题“松鹤齐年”一匾以示谢忱与交谊; 而张氏椎拓绝技绵延数代,后继有人,像四代孙张忠发就曾是汉中博物馆特聘“石门十三品”首席椎拓技师,抵今张门犹有传人继承祖传手艺, 并已通过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核,正申报国家级“非遗”资格认证。
发生在晚清这次以椎拓高质量、大数额石刻拓片兼带一定商业性质的金石学活动, 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陈授、吴访、张拓碑帖的流通、互市、递藏,虽然是否确信经光绪年间东渡扶桑金石学家杨守敬携往日本,尚有待作进一步鉴证, 但“汉三颂”拓本不乏为东瀛金石学家收藏显系不争事实。像日本知名金石学家中村不折就庋藏有传为宋拓,实属乾隆五十年前后石门所在地汉中褒城知县倪学洙募工椎拓《大开通》; 全日本书道联盟副理事长锺谷善舟亦弆藏大量石门摩崖拓本, 他不但三赴汉中参拜,1985年3月甚至即席挥毫题书“汉中石门,日本之师”,以示东邻书法、金石学界对汉中石门暨“汉三颂”摩崖的高山仰止。翌年四月,日本书法界泰斗、著名汉学家中田勇次郎也来汉上访碑,并即兴题诗一首云:蜀道摩崖隶草奇,天然古秀入神技。春潭千丈绿依旧,移得巉岩中外知。兹后,如牛丸好一、西林昭一等众多日本金石书法界代表团纷至沓来,驾临石门、西狭访碑、临习, 几络绎不绝于途,一时竟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
赘语
历代宦游蜀道学人与“汉三颂”摩崖研究,乃中国传统金石学发展一段缩影。古人前缘既结,来者怎续后缘,是摆在当今金石学人面前无法回避的沉重学术命题,尤其在友邦学人竞相来华访碑问道日益频繁形势下,这一现状更是耐金石学创始暨“汉三颂”所在国学人寻味深省的议题。笔者结合本文主题,特将目前金石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征候开列如下,权作重振金石学研究刍议,深望学界同寅暨有识之士就此疑难杂症共同把脉会诊,对症下药,以祈有千余年历史的华夏金石学回春振兴,重新崛起,是所至祷。
一、人心不古,风雅不再。金石学研究需有一颗好古之心,这一心态表现在研究层面是锲而不舍的探究,包括排除万难勘察访碑,千方百计求索旧拓善本,反复比对校勘研究等。而另一层面是自觉保护古迹以传之后人。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古来深受宦游学人保护的《郙阁颂》、《石门颂》摩崖在上世纪60年代末叶遭毁灭性人为破坏。《郙阁颂》竟因无任何级别文物保护资格,被无知莽汉修路爆破炸毁;尽管事后有识之士搜集残石异地拼合粘接安置于灵岩寺,与田克仁仿刻相毗邻,但整方摩崖几如遭毁容般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二、行业萎缩,人才不济,出版冲击。碑帖行业低迷、萎缩早隐现于施蛰存先生上世纪60年代中叶《闲寂日记》; 而如今民间类似吴大澂时代张懋功般拓工、裱工、碑估已如凤毛麟角,严重断档,经营千年拓、贩、销售一条龙业务几近终结,仅有北京琉璃厂的庆云堂和中国书店,以及上海的朵云轩和上海书店屈指可数,而其经营部门也以库存老本坐吃山空。
复兴金石学动议虽好但任重道远,以上笔者梳理历代宦游蜀道学人跟“汉三颂”研究关系,特别是陈介祺与吴大澂为“三颂”访碑、传拓、研究而进行的一系列金石学通信,目的正是使一切有志于金石学事业(不啻古之宦游)的学界同寅胸怀使命感,对远去的盛况,低迷的现状和不甚明朗的前景认识、了解得更加自觉、警醒和紧迫,进而谋求解决计划、措施与方案,逐步实现金石学由施蛰存先生笔底“闲寂”而达“昭苏”的既定目标与良好愿景。(编者注:赘语部分有删节。)■
(本文撰写过程中,荷蒙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童衍方先生指教,谨致谢忱。)
- 上一个宝物: 民国海派女画家群体管窥
- 下一个宝物: 齐白石对话李苦禅:丹青妙写齐派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