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使中国艺术史成为一门世界学问
 高居翰对晚明画家张宏有着极高的评价,图为张宏《青山绿水图》。
高居翰对晚明画家张宏有着极高的评价,图为张宏《青山绿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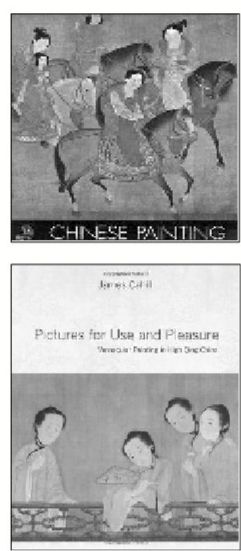 高居翰将在国内出版的两本新作的英文版封面。
高居翰将在国内出版的两本新作的英文版封面。
评价高居翰
1992年,洪再新到伯克利艺术史系和中国研究中心访学,有机会接触到高居瀚,深受其研讨班教学模式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回国后,洪再新到中国美术学院教书,便把高居翰的治学方法及教育方式带入到课程当中。其时,高士明即是洪再新课堂中的一名学生。现在回想当初,高士明认为高居翰的思考与教学方法,对自己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高士明已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从高居翰到洪再新再到高士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师承关系下,在学术的对话与批评中,获得了推进与发展。
【方法】
在跨文化的框架和语境中做研究
新京报:你谈到洪再新从伯克利回来之后,带来了高居翰的治学与教育方法,能具体谈谈这种治学和教育方法吗
高士明:我90年代初来到美院读书,从本科一年级就开始进入研讨班的状态,这在90年代的绝大多数大学只有研究生课程才会这么做。而且在第一堂课上,洪再新教授就给出我们一张多元文化的历史年代表,和一张文化历史地图,就是说一开始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时空坐标,让你知道你在时间上、空间上处于哪个位置,这就让你的知识相对化了。这一点对我本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高居翰一直在跨文化语境中做研究。
高士明:对,跨文化,贯通中西两个脉络。为什么他的研究会有很独特的视角,甚至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并不认同,是因为他给你构造的框架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框架和语境的意识。我一直觉得非常幸运,我在本科一年级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两点,你的研究、思考问题的语境、上下文是什么,框架是什么,用怎样的框架去看、去论述,这其实是很关键的,这两者构造了你的问题意识。我觉得以现在的眼光回想起来,当年洪老师从伯克利回来把高先生的教学方法、工作方法传递到我们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受益最深的一个是把所有的知识相对化,另一个就是语境、框架、问题意识这三点,这三点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是更重要的。
【视角】
将艺术史纳入社会史的范畴内
新京报:我们回到具体的中国美术史的角度,高居翰带给我们的主要贡献是什么是不是把美术史纳入到了一种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中来研究。
高士明:主要是社会史。其实中国的历史学以前仍然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的,我们的历史意识是这样的,只有朝代更替,而没有社会史缓慢地演进,而中国美术史尤其深受传统正史的影响,基本像帝王本纪或列传那样讲述艺术家,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格史。高居翰先生认为艺术的风格史是从社会史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的风格背后不只是风格即人这样单一的说法,而是有着现实的协商,各种文化因子的相互作用。他用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视角,看得比我们要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更加符合历史的发生。
新京报:洪再新老师提到高居翰的视觉命题,就是他的研究是图文并举的,而国内一些研究更偏重于文献记载,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补充
高士明:我们注重图像的时候往往会引向鉴赏,就是对作品的品鉴,研究则比较多地注重史料。我们中国很多年轻学者或学生,说白了就是解读图像的能力其实不够。我们解读图像的时候似乎就是在用鉴赏家的语言说,哦,这一笔画得多么精妙,用笔如何等等,但是这个图像如何说话,如何成为历史线索和重要证据,图像和图像之间超出风格史的内在关联说明了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以前的美术史研究比较欠缺的,但在高居翰的研究中他很强调这些东西。
【发现】
他挑战了传统文人画的判断
新京报:高居翰对17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是最为人称道的,范景中老师曾说他唤起了我们对17世纪一批奇趣山水、再现山水作者的整体认识,他唤起的是怎样一种认识呢
高士明: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认为17世纪一些图像是等而下之的,而高居翰先生作为美国的汉学家实际上有些批判性地挑战了我们传统的文人画的说法、价值。在他的历史细读里,他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奇绝山水,以前不被认可的、很边缘的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价值、意义、魅力所在。我想引申一下范老师的论断,高居翰先生本人和他这一代人实际上对中国美术史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能很简单地看,这些海外汉学家提供的视角和理解的框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他就比传统史学更加了不起,而是说他的工作为中国的艺术史研究成为一门世界学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新京报:能谈谈高居翰对于晚明画家吴彬和张宏的重新发现吗
高士明:这两个画家在高居翰的研究之前在艺术史中都是非常边缘的,可以说一般的艺术通史中都很少提到。高居翰发现吴彬和张宏,不是在艺术史名单中增加了这两个人,而主要是通过对这两个画家的研究带出了我们以往所认为的一个比较贫乏的世纪。在我们传统史学的框架和叙述中,吴彬和张宏的世纪被认为的一个贫乏的世纪,而高居翰对他们两个进行的个案研究恰恰证明了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创新能量的时期,同时也反证一般传统文人画价值系统、价值观的缺失。缺失的部分遮盖了些什么东西,这是最关键的,不在于这两个作家被关注,价格变得很贵,美术馆开始收藏,而在于他在史学叙事上的贡献,以及由此对那个时代传统审美价值观一个重新的认识。
新京报:我觉得高居翰的历史研究是很有想象力的。
高士明:历史学家是需要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不仅需要严谨的史料功夫,更需要想象力,历史学家的想象力不是从无到有,而是要想象出一个模型。我的师祖说我们每个历史学家面对的都是一堆碎片,如何用碎片构造出当年的器物,碎片永远是不完整的,只有器物的三分之一,如何去构造它,这时是需要想象力的。这和艺术创作的想象力不同,而是使历史素材成像的能力。
■ 声音
@三联学术通讯豆瓣小站:
面对突然间的生死之隔,最遗憾的就是自己还有很多未竟的事情——没能让高居翰先生看到最后两本中译本著作的出版。说来也巧,这两本书的英文原版,一本是他年轻时的成名之作,一本是他晚年的收官之作,两本书对于他自己以及读者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两本书分别是:《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与《致用与娱情的图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 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编者注]
@潘二如:高居翰的收藏品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有些不妥;而他说《溪岸图》是张大千伪造的,否认是五代董源的作品(是否为董源,当然还是个悬案),这是我曾经最难以接受的一个观点。当然,高人已逝,我们还是多看看他的著作,多看看他著作中的好!期待他的成名之作和收官之作早日出版。
@朱万章:惊悉高居翰先生仙逝,美术史学界又损失一泰斗级人物。高居翰的中国绘画史研究成果,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绘画的流变提供了不同的视觉。记得最早涉猎其学术论著是其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后来陆续读其《山外山》、《江岸送别》、等,其研究的角度、观点可谓别开生面,令人豁然开朗。
@徐坚_JX:非常震惊地看到中国艺术史最伟大的学者和老师之一高居翰去世消息。他的未竟著作已成悬念。中国书画研粳尤其是元明书画上,将用很长时间才能走出高居翰话语。
@-ici:高居翰教授去世,沉痛悼念。相信他是无数人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启蒙者,我也通过邮件受过他的不少指导。
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