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的水与墨:只有黑白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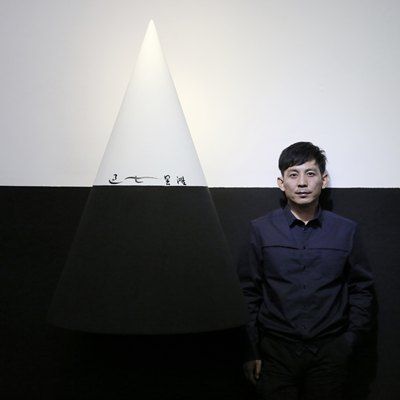 马军的“水与墨”
马军的“水与墨”
文/宋诗婷 <<新周刊>>第419期
展览现场没有传统文化和水墨字画,有的只是黑与白的对峙。马军打破了传统的水墨概念,构建出一个“水与墨”的场域。
马军把心怀“水墨”期待的参观者戏弄了。他的“水墨”以整个画廊为创作对象,是一次基于现有空间的规划和设计。
4月6日,“水墨——一个主题的语境实验及体验空间”展在798的3画廊开幕,展览现场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个空间里,马军筑起一面用工业泡沫3D雕刻的中国传统院落的白墙,一段死去的树枝被白色石膏包裹,悬于与院墙等高的位置。纯白的十面体石膏稳坐在墙面左下角——两个空间的交合处。
展厅内侧的空间营造出一个“水墨”现场。四面墙壁在1.6米的位置分界,下面是属于墨迹的黑色,上面是属于墙壁的纯白。正方体、圆锥体、球体……七个几何形体或悬浮于空中,或安置于地面。它们浸染在“墨池”中,与墙壁一样呈现出黑白两色。灯光映射在墙面与几何形体上,投射出亦真亦幻的光影。
展览现场没有传统文化和水墨字画,有的只是黑与白的对峙。马军打破了传统的水墨概念,构建出一个“水与墨”的场域。走进马军的作品,是走进被装饰的空间,是走进水墨池,也是走进对自我的探索。
对马军的采访在画廊的后院进行。从展览开幕到采访当天,马军很多时间都待在画廊里,一来是招呼朋友,二来是接收参观者的反馈。马军甚至在暮春那天邀请朋友在展览空间“雅集”,把坐垫摆在白色墙壁和枯树枝下,读诗,聊天,喝啤酒。“人是这个展览很重要的一部分。”马军说。
从“新瓷器”到由三个空间组成的别院“境”,再到今天的“水墨”实验,对于马军来说,从前,空间是一座座雕塑,现在则是一个个可以被操控的“境”。
雕塑家对空间有着天然的感知力,高度、宽度和整个空间所散发的气场吸引着马军去与之对话。从雕塑到用雕塑填满空间,马军的视野从一个个具象的物质转向抽象的控制。“一个空旷的空间,你把一个东西放进去,填充它,改变它,它对空间的占据能够改变气场、形态,进而延展出探讨的可能性,这是我现在感兴趣的。”
马军心中的平面不是有边界的白纸,而是一面白色的墙壁。
去年年底,马军接到一个平面展览的邀请,希望他创作一个平面作品参加展览。“我是雕塑出身,这为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平面、空间,以及平面与空间的关系。”马军说。
马军心中的平面不是有边界的白纸,而是一面白色的墙壁。“我用什么来填充它?让作品的气场能够压住这个空间,与空间形成互动?”马军一直对白色的墙面着迷,“一幅画摆在那只是一幅画,与白墙能够带来的空间和想象力无法相比。”
肌理与时间的共谋是白墙的语言。于是,马军打算用自然凝固的石膏做一面白墙,制作过程中,任何偶然留下的痕迹都是自然的记录过程。“然后,我要怎样与它对话呢?”雕塑专业出身的马军习惯了空间思维,他将几何形体与白墙并置,二者的结合只有一个脆弱的交点,彼此依赖,却也呈现出临界于彼此分离的不安全感。
“还缺一种东西,一种变量的东西。”马军说。于是,他把石膏白墙和几何形体一起浸染在墨池中。出水的作品多了层意境,浸没的高度对石膏板和几何体统一进行了分割,白墙有了故事。
这组平面作品马军做了三个:球体、圆锥体和圆柱体。他喜欢这些简洁的黑白作品,却还觉得不过瘾。“我希望把这种概念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表现出来。”马军说。
在798的展览中,计划中的水墨池没有填进流动的液体水墨,而是用涂抹在墙上的水墨营造出墨池的意境。原本的一个空间也变成了两个,在计划外的另一个空间里,马军发展了曾经的空间作品《境》,取名为《界》。作品将藏在墙内的树枝搬到了墙外,并把无法融于中国意境的几何形体引入空间。
从《境》到《界》,马军在回避原来的自己。他说,这几点改变打破了原本的人文氛围,抹去了文化属性和地域属性。
马军在感性的艺术创作中追求相对的冷静和客观,“所以,里面的黑白之境才更纯粹,更剔除了现实、虚拟、文化和传统。” 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个问题成就了中国艺术家,同时也困住了中国艺术家。
“先不要讲那么多主义,不要讨论新水墨、新表现还是旧表现,与其造概念,不如我们回到原点,重新思考艺术和创作还有什么可能性。”马军说,《水墨》是他源于“放下”的尝试。
“‘新瓷器’表现的不是装饰,而是文化的包裹。”
马军的“新瓷器”把象征着消费主义的电视、汽车、奢侈品制成仿古瓷器,摆脱了物件的使用价值,也抛弃了瓷器的使用价值,只留其观赏性。有人说,在东方瓷器中融入西方的消费文化,中西结合的同时,融汇古今,是种讨巧的创意。
马军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自己1974年出生,1978年改革开放,成长伴随着物欲的膨胀。“我看到了电视、录音机、电脑,之后又看到了LV、香水和各种奢侈品,它们组成了我对于消费文化的最初理解。”马军说,他做了他所经历并给他留下记忆的东西,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像消费文化伴随着我的成长一样,‘新瓷器’表现的不是装饰,而是文化的包裹。没有谁比谁强,它是对等的、公平的对话。”
“新瓷器”对马军来说,更像是一种调侃,这符合他不温不火却“蔫儿坏”的双鱼座性格。
“新瓷器”把消费主义装进瓷器,“瓷书”为西方的思想武器披上瓷衣,“瓷·肉”把鲜肉定格……马军一系列瓷器作品为他在雕塑界内外赢得了声誉。
“水墨”展览之后,马军的“瓷·肉”将在德国柏林展出。德国的展览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力上都远高于“水墨”。但在马军心中,“水墨”的意义却远胜于另一场展览。“德国的展览是我瓷器作品的推演,逻辑上是相通的。但‘水墨’是全新的尝试,我更看重它的不确定性。”马军说。
为了增添“水墨”实验的不确定性,马军为它加入了几组“变量”。
采访当天上午,一场对谈在“水墨”空间展开。策展人柴中建与哲学博士陈岸瑛在空间内展开对话。二人分别着黑白两色的衣服,相对而坐,在空间内说空间,在艺术的语境下探讨哲学。
“思想也是一种材料,也是对空间的介入。哲学命题与空间并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马军说。
首次“变量”尝试很成功,马军开始尝试在空间中融入更多的不确定性:何清的行为艺术、东妮尔的当代舞、子曰秋野的音乐行为,还有Muse、烨子、宋昭的即兴音乐表演。
前一天音乐人子曰秋野在表演中留下的书写痕迹还在墙上,第二天Muse组合的即兴音乐表演又在“水墨”空间内进行。长笛、古筝和大提琴相互呼应,声音触碰墙壁、几何形体和观众,萦绕在有限的黑白空间内。
自由人声表演艺术家烨子也介入了。她隐藏在四棱锥体后歇斯底里地呐喊,对着墙壁哭泣,在正方体前低声吟唱……伴随着大提琴艺术家宋昭的演奏和空间的转移,烨子时而悲切时而平静。三台录像机记录了艺术家们的现场创作。
“空间就是这个样子,有它的不确定性,空间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馈。声音、动作和思想是人最基本的东西,我尝试把它们作为一个文本保存下来,这或许是这次展览最有意义的部分。”马军说。
这是一个空间作品,观众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空间的渲染
《新周刊》:“水墨”里的水墨意境和传统水墨艺术有什么不同?
马军:这里的水和墨就是两种物质,它没有水墨所附带的那些传统和厚重的文化属性,它不东方,也不写意。我希望把话题拉回水墨本身,把那些附加在上面的东西剔除掉。
《新周刊》:为什么选择在空间内放置几何形体?
马军: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数个几何形体组合而成的,世界万物都可以归纳为几何形体。几何形体是推演出来的,是理性归纳出来的。这个是球体,那个是立方体,这是受光面,那是投影……几何形体构成了我们对空间最初的认识。
《新周刊》:参观者在这个作品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军:这是一个空间作品,不是平面也不是雕塑。对空间的感受不只是三维的,这中间有意识的存在。这个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是独立存在的,每一个观众进入这个场域都相当于进入一个大型的墨池,和墨池本身产生关联。不管你是一个普通观众,是音乐家,还是舞蹈家,在这个空间里,你所有的呼吸、动作和语言都为空间填充内容,是对空间的渲染。
《新周刊》:这个作品在你的创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马军:这个作品是我创作线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做减法,把一些附加的东西去掉。“做减法”也是雕塑的一个核心概念,雕塑就是把不要的东西剔除掉,只留下想要的东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剔除符号性,区域性和文化性。所以你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不会识别出这是哪个国家的艺术家做的,它是一个对本质问题的探讨,又是不确定的。
《新周刊》:现在的创作和之前“新瓷器”有什么不同?
马军:“新瓷器”首先具有观赏性,是我对西方文化的反应。西方的东西,一个力打过来,这个力量很强大,很有魅力,我要接受它,但不能被它吃掉,要再把它打出去。这是一种力的关系,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是种博弈。而现在,我不再纠缠于西方、东方、传统、现代。我感兴趣的是对空间的理解,我希望这种理解是超越时代的,是对人类共同性的思考。
- 上一个宝物: 谷文达在佛山元吉黄公祠重振孝道
- 下一个宝物: 李静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