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西:还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对世界有意义的
 play
范西
向前
向后
play
范西
向前
向后
 范西:还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对世界有意义的
范西:还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对世界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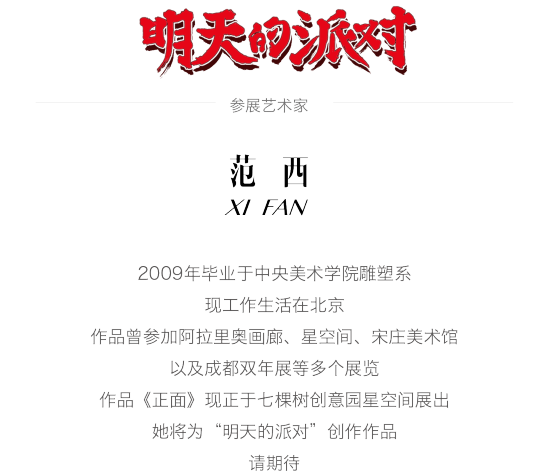 范西:还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对世界有意义的
范西:还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对世界有意义的
 范西作品《房间》
范西作品《房间》
“Today聊”做到第三期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已经开始自然生长了。因为它能如此反映一个艺术家的性格,而这种独特性格的背后又有着人类部分的共性。
就说范西吧,她是吴笛之外,给人的另一种直觉反应,不同的是,这种反应以某种本能的反抗作为基础,比如,她大概是所有人中最多质疑“你这都是什么问题”的人。她也直言:“我反感一切应付的东西,没有真正认真考虑过的事情和只用眼睛做判断。”
范西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却选择了摄影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她曾经在和老师向京的对话中表达了她为何要转向摄影的原因:“很多东西都会‘过去’,摄影表面对应了这个过去,同时它也抓住了相对‘过去’的东西。”
她的摄影作品《正面》正于北京七棵树创意园的星空间展出,这是一组12个女同性恋者赤裸上半身的照片。她们的表情都略显严肃,其中一些人的神情中甚至表现出强烈的痛苦和自我防御。拍摄这个项目她花了四年时间,因为“创作是个严重的事,不是个轻易的‘咔嚓’”。
雕塑系学生的形体素养体现在了她的摄影作品里,比如《房间》,但我们更喜欢她在作品《平行》里所表达的"在水这种介质中,卸去防备后的真实"。 某种程度上,范西的作品和我们的采访一样,都希望还原部分的真实,尽管我们也都承认人的复杂和多面性。
由于她作品中如此强烈的性别意识,我们也顺便聊了聊女性主义和身份的话题,对此,我们都很坦诚地表明自己的感觉――正如我们启动这个采访项目时所宣布的:感觉是自由的。虽然有些对话看似偏离了“有趣、好玩”的形式设定,但不能不更同意范西所说:“有趣、好玩和打动你是两个层次。”
鉴于我们是如此擅长激怒像范西这样认真较劲的艺术家,导致这场谈话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我们想要的、介入最深的采访状态。有好几次,甚至觉得是我们在接受采访,NND!
T=忒逮
F=范西
F: 说下你的问题,(瞟了眼采访提纲)八个。
T: 你最近觉得比较荒谬的一件事是什么?
F: 就这事(“明天的派对”),不知道点在哪儿。
T: 你曾经为什么事自卑过?
F: 你这是什么问题?自卑,下一个呢?
T: 这个不回答是吗?
F: 可以回答。
T: 你先回答这个吧。
F: 没有曾经,一直都很自卑。这也许不是自卑,是一种要求。
T: 为了让不喜欢你的人感受到你的恶意,你都做过什么?
F: 不喜欢的人就不会接触了。看不见,更不必让他感觉到任何。
T: 什么是艺术家?
F: 我觉得艺术家跟其他行当一样,从事艺术职业的,算是一个工种,需要持续思考的工种。
T: 你怎么评价你的作品?
F: 评价我的作品?我觉得需要时间静下心慢慢看,它们比较细腻,没那么多视觉感应。它不是刺激至少不是视觉刺激, 眼睛跟心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的东西里有一个距离,需要时间到达 ,但现在很多人都缺少耐心。
T: 如果不做艺术家你会做什么?
F: 厨师,或者做保洁阿姨。
T: 为什么是保洁阿姨?
F: 因为我爱打扫卫生。艺术家,我觉得这个词对我来说挺重的。前几年不太轻易说自己是艺术家,它应该有一个持续思考的时间和过程。然后有可以自我肯定的作品。怎么说呢,我觉得做有趣的事容易,但是做艺术很难。你之前提到的有趣、好玩跟打动你,其实是两个层次,前者属于兴趣事,后者就有要求了,怎么才能在一个兴趣事里跟所谓的艺术结合,如何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因为艺术没那么简单,单靠兴趣支撑不了,所以一直觉得“做艺术”跟“是一个艺术家”存在一个标准,也不可能“人人都是艺术家”。
T: 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曾经特别相信,但现在会特别怀疑的吗?
F: 没有,很少。我金星摩羯,特别主观,就是相信某个东西会一直相信,很少受到影响。当然这也会造成些缺陷,会导致审美太单一。
T: 你是否觉得你自己的作品事实上对于这个世界上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没有突破的?
F: 常常觉得是。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如果你能坚持做一件事情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达到理想的结果,哪怕只是到达到一个阶段也好,又或者是你解决了某个问题,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像花了心思撬开一把锁……都是值得庆幸的。什么问题来着?我忘了。
T: 自己的作品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F: 我还想不到有什么东西是对世界有意义的,世界太大了,人又特单薄,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经常觉得一切都是跟你毫不相干却又时时被牵扯着处于其中。就像是纪录片《轮回》,它在不停地转动、重复,不会因为什么事或什么人而改变。 而大多数艺术家不是在创造自己的世界就是在拉拢别人进入到自己已经创造好的世界里,但都不是那个独立存在的整体。 即便想改变,也很难讲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重点不是考虑意义的问题,而是你的选择,如何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并且尽可能的做好。
T: 你会有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最终发现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但它就变成这样了吗?
F: 经常这样,毕竟它不是机械生产,预设跟结果不可能等同。你规定好尺寸、材质等等,结果就理所当然的出现,这种情况很不现实,就算有可能,作品也会成为没有生命的机器。人是复杂也是变化的,而你的创作过程中不光有人,所有的物件都是活的,你不可能掌控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人跟物都应该是平等的,只能说我接受它在过程中的变化,也知道排斥的是什么,所以它不可能变成另一种东西。变化当然也是创作过程的魅力。
T: 什么是你的底限?绝对不能碰的那个点。
F: 个人问题吧。底限,对,不要八卦。这个问题就很八卦,你为什么会想问底限呢?
T: 可能它会在你的艺术作品里也表达出来。
F: 我觉得不一定,艺术跟生活有时是分离的,它也有段距离,确切的说是比例,这也只是对我来说,有的人生活可能就是他的艺术,艺术也是他全部的生活。
T: 你觉得自己内心中是一个女性吗?
F: 我不用内心,我完完全全里里外外都是,当然啊,太明显了。
T: 你在生活中或者是朋友面前会是一个强势或者独裁的人吗?
F: 我倒不觉得,但是别人都说有。比较自我吧,可能是。
T: 自我是好事吗?
F: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生活问题还是哲学问题?我觉得自我挺好的,我认为艺术家都挺自我的,有好有坏,生活上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艺术上就需要这样的自我,因为自我才能不被影响而专注地工作,你要考虑太多就太容易分散。
T: 你有要反抗的东西吗?
F: 反抗?有啊。我反感一切应付的东西,没有真正认真考虑过的事情和只用眼睛做判断。
T: 我好像没有问题了,你还有问题吗?
F: 没有,我觉得我的话都可以剪掉。
- 上一个宝物: 吴笛:我没有非常相信的东西
- 下一个宝物: 华晨宇:我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