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上绘画渐式微多媒材大有可为
 方力钧 《2013.7.9》(陶瓷装置)
方力钧 《2013.7.9》(陶瓷装置)
 方力钧 《2013》(布面油画)
方力钧 《2013》(布面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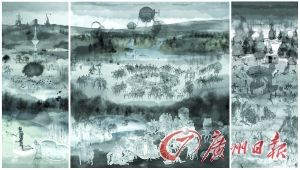 缪晓春 《坐天观井》(三联画+数码水墨)
缪晓春 《坐天观井》(三联画+数码水墨)
 岳敏君 《表皮12》(布面丙烯)
岳敏君 《表皮12》(布面丙烯)
文、图/ 金叶
在蔡国强用火药引发《爆炸系列》、徐冰用破铜烂铁打造《凤凰》频频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同时,国内许多本是以架上绘画成名的艺术家也开始纷纷涉足多媒材创作。促使艺术家们集体“跨界”的动力来自何处?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多媒材必然具有超越架上绘画的能量吗?架上绘画亘古不变的魅力是否正在衰减?借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的契机,记者采访到了前来参展的三位跨界艺术家,并诚邀评论家刘骁纯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艺术家 方力钧——
尝试多媒材是艺术家的好奇心使然
我做装置大概始于2006年,用过的材质也比较多,垃圾堆的瓶瓶罐罐,钢的、树脂的、塑料的材料都有用过。你问我为什么进行多媒材的尝试?动力也许就是一颗属于艺术家的好奇心。
这两年我开始做一些陶瓷的立体作品,其实我十五六岁读中专的时候学的就是陶瓷美术。正因为学过陶瓷,所以很长时间里我对陶瓷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化的看法,觉得它作为一个很完善的系统,会产生很强大的约束,所以我本来不太想碰它。但这几年,也许是常在景德镇待着,慢慢又对这种材质产生了兴趣。我觉得已有的陶瓷作品很少和我们现实的场景有直接的关联。而作为艺术家,用传统的材料来表达当下的情况和人的心理、精神状况,其实特别有意思。
我也想明白了一件事:传统的陶瓷体系固然是一种约束,但我不去遵守它不就行了吗?大家会看到我现在做的陶瓷作品和传统很不一样。它们基本是一些小的陶瓷立方块的各种组合,这些小小的陶瓷块在传统意义上都是些“废品”和“垃圾”。而我选择使用陶瓷的基本单位,深入挖掘其物理可能性。烧造的过程也和传统不一样,是将湿的陶泥直接进炉,出来的效果是各种歪歪扭扭的状态、坍塌和变形。水和泥、水和火、泥和火,不同釉色的收缩,带来各种不可预知的变化,让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做一件器物,而是在做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尽管我现在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创作实验性质的作品,但绘画对于我的吸引力仍然巨大。多媒材和传统媒介是一种互相促进、良性循环的过程,就像吃火锅:吃得越辣,你可能需要喝更多的啤酒,而喝啤酒其实是为了更多地吃火锅。很多时候,我做着平面的事情,却在考虑立体的问题,做立体实验的时候,又在考虑平面的事情。有了这种互相印证、促进的关系之后,我现在对于绘画的认识可能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在多媒材的时代里,绘画依然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它的体温和气味,那是一种生命最本质的因素。这样一种“体温”,还是必须要靠传统的、手工的方式来完成,而不是机器和电脑。我们的技术也许可以做出各种栩栩如生的模特,但我们知道那是程式化的,我们终究还是渴望知道真实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相信,在多媒材蓬勃兴起的当下及未来,传统绘画不仅不会消失,还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我们去储存大件的、立体的作品的成本代价会越来越高。如果平面艺术品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不亚于立体的艺术品,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那些成本很高、占用空间更多的艺术品呢?
艺术家 缪晓春——
选择最合适的媒介来表达特定的主题
1995年~1999年,我在德国卡塞尔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专业虽然是造型艺术,但油画、雕塑、影像等内容也都有所涉及。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并不太注意艺术媒介之间的差别,而只是强调选择合适的媒介来表达特定的主题。
从1988年至今,我大概每10年就有一次转向:1988年到1998年主要是绘画;1999年到2009年主要是摄影;而现在主要是数字媒体创作。电脑、软件、鼠标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笔、墨、纸、砚。既然是我们天天在用的东西,当然可以成为艺术表达的某种途径,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独特的使命。新媒介确实可以做到一些传统媒介无法做到的事情,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比如我正在做的“数码水墨”:我的模型是用点、线、面来建立的,这个点、线、面本身就很有美感。建构完成之后,再加上一些晕染的效果处理,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水墨方式,这也是我现阶段比较感兴趣的。
我相信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将来的表达方式会越来越多。我们难以想象在一百年之后会有多少种表达的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表达方式越多,针对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主题,就会有更适合的表达媒介。但我并不认为某种媒介一定比另外一种媒介更好的说法。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只有“更合适”的媒介,没有“更先进”的媒介。
传统的媒介当然会一直存在下去,无论水墨还是油画,都是不错的表达方式,而且传统媒介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2009年以前,我做了很多摄影作品,但2009年之后,我很大一部分精力又回到了绘画上面——即便目前是用数码的方式在做。这类某种程度的“回转”,也是因为我看到了绘画这种传统方式仍旧具有可能性,否则我不会这样去做。
艺术家 王广义——
不太懂的新手段不会贸然尝试
我是国内比较早开始进行多媒材尝试的,1984年就开始做装置了,这方面的实践一直持续至今。也没有什么“触发点”,就是源自一个艺术家的本性,对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东西都想去试一下。
这几十年来,各种媒材越来越丰富,但我觉得自己是停留在胶片时代的人。胶片时代的东西我看得懂,但进入数码时代,我觉得我不太懂了,所以不会贸然尝试新的手段。而且,我也不觉得一个艺术家需要掌握太多的手段,那样会很乱。现有的媒介在表达我想表达的思想方面,没有不够用的感觉。所以,我的表达手段并不面临需要更新换代的问题。
本质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现在我的精力和时间,分配在绘画方面的还是最多的——大概占到七成,我相信绘画是无法被取代的。对我而言,这里面让我最难割舍的也许是“手感”的问题。即便我做的装置,其实也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物”的感觉。某种程度上,它们和我的绘画作品一样,都是向手工时代致敬的产物。
我也有一些好朋友,做新媒材、影像,做得很好。但我还是愿意选择一种和手工相关的方式,绘画或者装置——我并不认为这个一定更高明,但我自己更有兴趣。
我不明白为何有人担心绘画会消失。绘画是一个最古老的存在,今天的艺术家,可以用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也可以用装置、用影像……它们之间不应该有界限。担心绘画会消失就像担心人类会消失一样,是根本没必要的问题。
评论家 刘骁纯——
穷途末路的不是架上绘画
刘庆和黄一瀚就是有益突破的艺术家
国内许多以架上绘画成名的艺术家,这几年开始更多地进行多媒材的尝试,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般来说,对艺术史有比较大贡献的艺术家,思想上的条框通常都比较少,总是在一方面取得突破之后,就在另一方面进行尝试。
比如德国表现主义的绘画大师,基本都是在绘画的同时尝试做一些雕塑、装置、多媒体等,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基佛尔,画画、综合媒材、装置、表演等,都很厉害。不过一般的艺术家没必要去效仿他,还是选择一种自己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艺术就可以了。
这种优秀艺术家普遍性的“跨界”,不意味架上绘画正在失去可能性。现在经常有人说在欧美国家,架上绘画的版图已经非常萎缩,也是一种误解。其实包括威尼斯的双年展,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量的架上艺术。我这几年重点研究水墨,水墨的架上这块,也有很多艺术家取得了有益的突破,比如刘庆和、黄一翰,都是很有创意的艺术家。架上艺术不会过时,在未来仍是大有可为的一片疆域。
但我所说的这种富有前景的“架上艺术”,和我们国内目前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仍旧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架上艺术风貌又不是一回事。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张晓刚这一批画家,他们当年的绘画因为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所以产生了巨大的意义,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他们当年选择的这种带有极强符号色彩的道路,既为他们赢得了成功,也推着他们走进了今天的困境——他们很难在这个符号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取得更大突破,这也逼迫他们开始向装置方面转型。虽然目前来看,力度没有蔡国强、黄永砯那么大,但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比如方力钧,我一直认为他是在当代艺术中做得比较出色的,他敲开了一扇门,但没有一直停在门口,而是一直摸索前行,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符号性弱了,声名也有所下降,但也许过上十年我们再回头看,他可能会是探索中最厉害的一个。
- 上一个宝物: 不吃透西方艺术谈何超越
- 下一个宝物: 名人信札手迹拍卖市场泡沫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