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一颗闪耀的星
 常任侠
常任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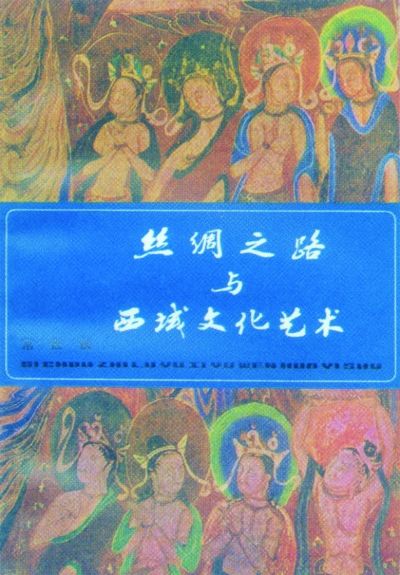 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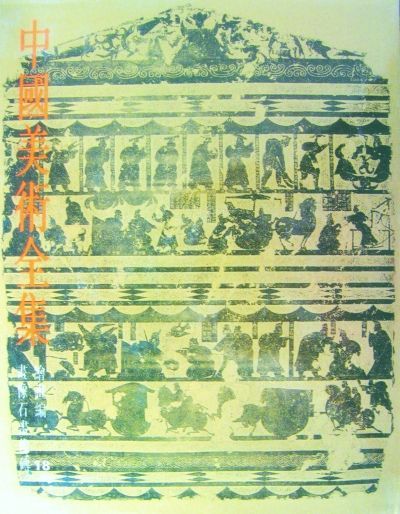 常任侠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画像石画像砖》
常任侠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画像石画像砖》
本报记者 胡立辉
人物名片
常任侠(1904-1996),安徽颍上人,著名东方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学家、诗人。
1935年赴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研习东方艺术史。“七七”事变后,历任《抗战日报》编辑、武汉军委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联络秘书、国立艺专国文教授、昆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长。曾赴印度国际大学任中国文化史教授,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有《民俗艺术考古论集》、《中国古典艺术》、《东方艺术丛谈》、《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常任侠文集》(六卷本)等。
巡礼在东方艺术的画廊中,常任侠无疑是这悠长画卷里一颗闪亮的星。作为20世纪致力于东方艺术研究的美学家,常任侠建构了颇为独特的艺术研究模式和理论范式,他基于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索,进而在巫术与艺术起源、中国美术史的重建、表情艺术理论的拓展,乃至东南亚艺术形态和艺术理论的交流融合等层面多有建树,为20世纪的中国艺术理论升腾出别样的东方色彩。
北大南亚所的研究生、美术理论家王镛当年曾求学于常任侠门下,他说:“恩师毕生治学精勤,涉猎颇广,文笔气势豪宕,不愧诗人本色。”日前,在北京某拍场上,“一角小楼画语温——常任侠藏珍”令众人关注到他,一位几乎与20世纪同龄的学者。
多面能手 求索问道
“早在儿童时代,我就爱听大人们讲故事,尤其爱听《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为这些幻怪动人的情节所吸引,往往忘记睡眠。及长,读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传记,深致敬仰,常欲追踪远游,一去印度。”孩童时的侠义梦想促动了常任侠的学术之路。
1928年,常任侠就读南大,师从汤用彤,初步学习了佛经和梵文。1935年去日本东京又研究了佛教艺术,益发增加了他去印度的迫切愿望。但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常任侠才有机会赴印度国际大学执教,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在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之余,常任侠利用假期到尼泊尔和不丹等国访问,并实地考察印度历史文化遗迹,比较印度的阿旃陀石窟与中国的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艺术遗迹之异同。他充分吸收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领悟文献材料的特殊感性,获得了从事中外艺术交流史研究所必需的田野考察知识。因而,他将文化交流、文物考古与艺术品考察三位一体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在视野、理论与方法上对于今人研究当代东方艺术史以及艺术考古学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常任侠从读书时期就表现出对一切文艺的热爱之情。他参加话剧表演、写歌词、写剧本、爱摄影、爱收藏……抗战时期他不仅为《抗战日报》编副刊,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还兼任重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艺术考古研究院任研究员,与郭沫若、卫聚贤、金静庵、胡小石等主持重庆江北汉墓发掘;又与滕固、宗白华、商承祚、梁思成、傅抱石等组织中国艺术史学会,撰写《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乐渐史》、《民俗艺术考古论集》等书稿。他的诗剧《亚细亚之黎明》,由冼星海作曲,曾在延安等地上演;他作词的《壮丁上前线》、《中国空军军歌》等成为抗战经典歌曲;他组织新诗社——土星笔会,出版刊物《诗帆》。他一生所写新诗共结成三个集子,《毋忘草》、《收获期》和《蒙古调》;而他更为擅长的旧体诗词约计千首,结集于《樱花集》出版。
艺术考古 画学操行
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中,汲取西方艺术理论和文化思想来审视中国传统艺术的学者不乏其人。然而,与主流学术意识和趋向不同的是,常任侠异常冷静地将自身的学术视野投向了少有人关注的东方艺术的百花园,其建构的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虽不足以系统化谓之,但却涉足多维,颇富理论价值。
常任侠不仅与同时代的其他美学家在学术兴趣上颇为迥异,而且研究方式上也大相径庭。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注重田野调查。因为从1920年开始,中国艺术史学和艺术考古学研究常着眼于出土文物的制作工艺,缺乏深入探究其美学价值的视角,常常停留在欣赏层面,缺乏体系化的理论思考,也缺乏文化学意义上的比较分析。
艺术考古学成为其一生进行艺术观照和理论衍化的主要方式,这主要源自他留学期间日本国内艺术考古学研究热潮的影响。可以断言,艺术考古学为常任侠敲开了管窥中国传统艺术形态的钥匙,是其运用外来学术研究模式进行本土艺术研究的主流路径。正是借用这一研究方法,常任侠探讨艺术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而为现代美学的理论架构提供了新的视野。
荷锄陇亩 未忘著述
常任侠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华民族在20世纪所遭受的所有苦难。如许多热血男儿一样,他积极投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一生两次弃文从戎,北伐战争期间加入北伐青年军,抗日战争中在武汉军委会三厅任周恩来的秘书,并与楚图南、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然而,“文革”开始了。在那段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期,常任侠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被称为“大军阀的走狗”……在造反派的监督下,他与著名画家李苦禅一起参加劳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日共挽一车,运煤千斤,朝夕辗转不停。”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北磁县西陈村附近的农场,荷锄陇亩,未忘著述,往往“日行五十里,夜写一千言,每晚烧尽一支蜡烛为止。”同年,周恩来总理派人前来慰问,常先生回首前尘,感念万分:“传来温语可融冰,远怀西陈一老兵。”幸赖总理关怀,常先生得以不再下场地劳动,有暇在村中写书。在昏灯草舍内走笔夜书的20万字书稿,“文革”结束后得以出版,即是对研究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颇具参考价值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
常任侠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一位革命者,但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位文化学者,一位艺术史家。即使在革命生涯之中,他对东方文化艺术的关注与研究工作也没有停止过。“愿身作茧永抽丝”是其逾90高龄在中日友好医院病房写下的诗句,也是他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
对于求学、东渡、抗战、远游,研究、教学兼及其他的历经悲喜的一生,常任侠曾说过:“我一生的研究,杂吗?谈古论今,横说中外,是杂。专吗?古今中外,不离其纲,紧紧围绕东方各国美术史以丝绸之路为重心,很专。”
故居湮没 收藏散世
因性格之豪爽快意,常任侠广结好友,艺友间书画往来颇多。又因其专业涉及考古,癖好便是搜集铜器、砖瓦、印章、古钱等小古董,自然是不折不扣的收藏谜。其数十载所藏佳品,凡轴、卷、扇、联,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包。曾有文章记述当年常任侠受周恩来派遣赴粤闽浙三省视察,旅途中不能多带行李,他宁愿减掉部分衣物,也要带上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文物。有时为了收购文物,弄得自己身无分文。
在“一角小楼画语温——常任侠藏珍”专场拍卖会上,常任侠收藏多载的丹青墨宝共87 件以专场的形式首次面世。藏品中有成扇47把,其中既有常公与周作人、郭沫若、田汉、老舍、顾颉刚等学者文人君子之交的见证,亦有其凭借渊博学养集珍纳藏的如张大千、齐白石、于非闇、金城、颜伯龙、梁启超、刘半农等艺坛、文坛名家圣手的精品佳作。
常任侠夫人郭淑芬对记者表示,此次拍卖原属情非得已。常任侠曾多次在日记及诗作中表达了对故土颍上县的怀恋:“在1922年的秋天,我驾着一叶扁舟,离开了这个生长我的家。我从此去开创新的世界,结束了幼年的生活。”一处大门、一宅两院,门前即是沙颍河,河中白帆点点……然岁月更迭,历经数十年风雨变迁的常任侠故居如今已踪影全无。现在,在常东学村能寻觅到的只有一块石碑,从背后他所题的文字有少许先生踪迹。
郭淑芬表示,早在常先生辞世的十多年中,她同家人都在与颍上县接洽,希望能在常任侠故土为其建立故居,并将捐献常任侠藏品丰富馆藏展陈。国内一些学者和诸多市民亦曾呼吁,能否在颍上县重建常任侠故居或建设常任侠纪念馆。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今业已耄耋之年的郭淑芬未能等到规划成形的消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 上一个宝物: 这个时代不宜提倡文人画
- 下一个宝物: 为啥郑州城市雕塑损毁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