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艺术骄傲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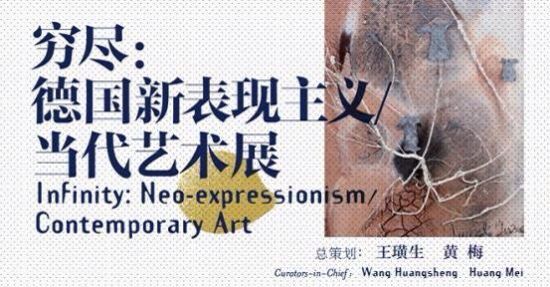 展览海报
展览海报
德国艺术骄傲的延续
北京展洲国际“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展”
德国是一个值得人尊重的国家:无论是他对历史的态度,还是他劫后重生的力量,更有一点,就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德国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人类的精神面貌。德国艺术不仅在欧美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可以说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以来都在不断的向德国汲取养分。
七月六日北京展洲国际带来了还不为大众所熟悉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展。在艺术上,从中古以来我们能够瞥见德国艺术注重个人、情绪、色彩和表现的特点。而在“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上更体现出了德国人的另一面:我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种疯狂的理性基因始终以一种热情而又自制的方式潜伏在德意志民族的血液中。
20世纪初,欧洲兴起了表现主义思潮,虽然在各国均有反映但表现主义思潮主要活动基地还是德国。挪威人蒙克直接推动了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从C·罗尔斯、L·柯林德、E·诺尔德到德累斯顿组织的第一个德国表现主义社团—“桥社”,表现主义逐渐在德国发展开来。1911年,以康定斯基和马尔克为主的青年骑士社团成立,此外还有《狂飙》杂志社和同名画廊。一战后德国表现主义社团主要是以格罗斯和迪克斯为代表的新客观社。
表现主义强调艺术语言,艺术的形式和表现力在他们那里有着做为伸展内在精神的重要作用,色彩、线条和形都有各自独立的表现价值。艺术家对世界的主观感受改变了客观世界原有的模样,或者说原有的模样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心灵体验、表现甚至是发泄,因此外在物开始变形、怪诞、抽象。
如果说在表现主义那里,艺术家还拘束在自己个人的精神世界的话,到了新表现主义那里,艺术家所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狭隘的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深刻的精神问题。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家突破了抽象主义的包围,在后现代主义纷繁且混乱的局面下呈现出一种绘画回归的趋势。但新表现主义仍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因为他决定自己回归绘画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推动了它作为新艺术的进程。
政治,是我们在新表现主义中能感受到的最明显的画面因素:马库斯·吕佩尔兹将纳粹的符号融入到画面之中,约尔格·伊门多夫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身份。这种对政治的自觉可以说是新表现主义的“标签”之一,同时它的“功用”在后现代主义之中显得格位显眼,如同伊门多夫所说“艺术家应该是文化的舌头”。而这里所说的文化,我的理解是特定时段的某个国家的文化,正是这一点原因才使得德国新表现主义彰显出了它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德国,在20世纪初的50年,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了全人类抹不掉的历史记忆。这个国家在战争不断的被毁灭,重建,而这样特殊的历史注定塑造出德国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思潮。这样看来对战争和历史的反思和对政治的思考无一不深刻的反映在艺术层面之上。艺术不应该回避政治,当然政治也不能完全成为艺术的指向。
因为这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关于正直、勇气和责任的问题,是关于一个人对自己生存环境和自己真正的生存价值考量的问题。人,应当是个人的人,应当是思想自由的人,应当是对自己的生存负责人的人。草木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生在哪里就长在哪里。
新表现主义不仅承续了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和怪诞,抽象的色彩,甚至被称为“新野兽主义”,更重要的是新表现主义是一种对表现主义的放大和超越。因为在这里,个人的精神体验首先不是被湮没或忽视,而是以不同的面貌保存下来,如乔治·巴塞利兹的突出特点将人物倒置(在《约克的左边和右边都是教堂》这幅作品中,倒置的人和正立的教堂显得十分诡异以及他著名的《倒置的鹰》),A.R。彭克对非传统西方符号的运用(《明星卫士》充满了原始意味的符号);其次,这种个人体验的影响放在战后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显得不那么个人,而是被突破和放大乃至成为整个社会情绪变化的反应。
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德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环境:东西两德分裂,各自站在美苏阵营之中对抗,西德经济落后,主权不完整,德国最高权力把持在“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阿登纳政府采取一边倒的国际政策依赖美国,战争的创伤加之邻国的不信任又使德国人形成了一种严重缺乏安全感又执意追求安全感的综合征。在不断重建与恢复的德国,弥漫的是一种不安、焦躁、反思、寻找的激烈气氛。百废待兴,一种新的渴望呼之欲出。
此时,新表现主义艺术家所表现出的那种民族情感,对历史的直视,对当下生存环境变化的思索,对政治的直接深入,不仅使艺术承担了更多的政治、历史、人文责任,艺术的“功用”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意淫”而是做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去参与去改变存在的社会(从这点上看,艺术功用的改变也促进了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打破);而且使德国在艺术上重拾自信——一种对艺术探索的“穷尽”的态度,一方面对抗“依赖国”美国在全球推行的波普等美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在艺术史上写下了德国所引领的辉煌一页。
“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穷尽了最具代表性的6位新表现主义大师,也让中国观众对新表现主义有了一次全面的体验和了解。
浊濯
- 上一个藏品: 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国际市场趋势分析报告
- 下一个藏品: 2013青年雕塑家邀请赛暨优秀作品展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