衲子先生的中国画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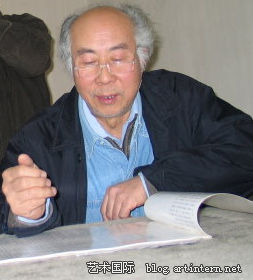 衲子先生肖像
衲子先生肖像
文|朱京生
在民国初年的学校美术教育中,中国画与素描大抵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激进的改良派重掌国立北平艺专以后,推行用素描来改造国画的教学,再加上解放后苏俄体系和政治的影响,作为中国画基础的书法不再被强调和重视,使中国画失却文化内涵和笔墨的精义,逐渐沦为一种技术,一种与其它艺术毫无差别的“造型”和“绘画”。六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教学体系没有培养出一位公认的中国画大师,中国画文化身份的模糊不清、写意精神的衰落、标准的混乱,根由在此。这样一种教学体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袁运生先生在《为什么要重建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访谈中指出:“按我们这种教育,再也出不了齐白石这种画家了,因为两个思路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基于对自己文明的理解……在这个体系下,同学们第一次接触艺术,首先同自己的文明产生关系,而不是一年级的时候就学西方……但是,看中国画系教员的画,有许多还是基于素描教学,还是和西方这个教育体系相关,好像很难与自己的文明产生联系……”其实,当中国画画家文化的第一口法乳变了,艺术的中、西体用关系变了,这个体系不仅培养不出齐白石,而且连王雪涛、李苦禅、李可染这样的大家也不再可能产生了,相反培养出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画的掘墓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衲子先生的中国画,和他所走过的——遵循中国画的内在理路和发展规律地去学习、创作的成功之路,开始凸显其现实意义与价值。其作品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欣赏、重视,我们认为,衲子先生遥接中国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淡泊名利,归隐于中国画的笔墨生活之中,以书法、诗心贯通画中,他的作品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表现了中国人儒雅、智慧、深沉、朴素、美丽的心灵和独特的审美观念,代表了当代中国画笔墨的高度,对写意画的发展有所贡献。礼失求诸野,今天回顾衲子先生所走过的中国画之路,对我们反思中国画教育和创作中的弊端,开启未来,是不无裨益的。
1.书法为基
衲子先生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道和命脉,它之于中国画是民族的选择,文化的选择,因此是绕不开的,更是打不倒的。而中国画笔墨的根基,是以书入画。
至少自张彦远以来的1000多年中,以书入画从实践和理论两条线索上都呈现一个渐强的趋势,所有成功的国画家无一例外都是优秀的书法家,可见书法已成为中国画生命和精神的共同体。诚如林语堂所说:“它是训练抽象气韵与轮廓的基本艺术,吾们还可以说它供给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进而石鲁在《谈中国画问题》一文中指出:“写字不好,就谈不上中国画。中国画必须是以书法、以中国特有的笔法来表现的。……中国画以书法作为它的基础,就决定了笔墨问题,决定了章法问题、布局问题,以至于各种各样的结构----也就是造型,都要随之而变异。这是一个规律,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将书法作为整个中国画的基础的认识,此前未必没有,但由石鲁明确提出来,触及到了中国画的本旨,意义重大。
衲子先生少即习八法,用功甚勤,有名于乡里。十六岁,欲从王雪涛先生学画,由一位师伯带着前去拜见,雪涛先生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老师,你先跟他学学书法。遂拜张惠中先生学书,张先生授以小篆笔法及兰竹画法,衲子自言:先生所授笔法,时间愈久,愈觉优越,受用不尽。其写字画画,执笔指实掌虚,不入关节屈曲处, 握管甚高,悬肘, 悬腕。
在国画实践和课徒过程中,衲子先生对书法强调的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他涉猎非常广泛,似乎于何绍基、《张玄墓志》、《张猛龙》、《嵩高灵庙碑》、《张迁碑》、二王、米芾等着力为多;其写字天分甚高,闲时读帖,于结构布置,行间疏密,照应起伏,正变巧拙,默识于心,下笔之际,点画无不自法帖中来,然后又能自成家数;临书往往第一遍能象,第二遍就变了,到第三遍已经是自己的了;很年轻的时候书法就过关了,其学生时代的字就令任课老师感到惊诧又自叹弗如;还喜用长锋羊毫,能驱使自如,八面出锋,从锋颖到笔根,全能力到,使柔如刚,每遇退毫秃笔,也运之自如,见者往往惊异;作书作画,无论大小,多半站立悬臂为之;又主张用大笔,力避小巧和细碎,得铺毫挥洒之趣;常喜作大字,且每每以大字佳否判书家高下,大约以为小字只是指腕间的事情,终不如悬臂挥洒能够畅机——画一大,就要求用笔,要求功力,书法要达到相当水平才行,有深入实践的人自能体会。
衲子先生的书法,已至碑帖融合之境。一方面,有拙、重、大的精神气象,笔笔周到,力透纸背,还时露净劲、老朴、古媚之趣;另一方面,也不乏松、灵、奇的特质,能飞提纸上,有魏晋风骨。他欣赏日本少字数一派书法,以为其中一些书家的字,是在写那个字的“字心”,每个字是有它本身的精神和生命,书写的人应该把那个东西找出来,这与中国的传统有关。其实每幅画的落款,也必有其应该有的要求,衲子画作落款,必据此别立一种意态,不主故常,且浓淡与画相呼应,令全幅统调浑然,开一新境界。《清水一钵见自心》、《芙蓉飞鸟》为其代表,后者画中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衲子”诸字,一片神行,浓淡变化精妙纤微,口不能言,与芙蓉飞鸟浑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纯是画面形象的一部分,令人拍案。
在笔墨精义所剩无几的当代中国画坛,衲子将书法透入画中,以他的生花妙笔于“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天真浪漫,风情万种,变幻莫测,开掘出中国画新的笔墨品质,使中国画的艺术语言获得升华。由此可知,雪涛先生当年将他推荐到张慧中先生门下去打书法的基础,是深有远见见的。
2.师承渊源
衲子先生十六岁从张惠中先生学习书法、兰竹,受到了严格正统的读帖、识字、研磨、用笔、用墨、用水、书写方法的训练,打下坚实基础,所得终生受用。十八岁考取北京中国画院画家培训班,师从王雪涛、汪慎生先生研习写意花鸟画,直至两位先生去世。
当时授课的形式,是由老师先讲画理,然后做示范,其中包括临摹、写生、创作三个部分;学生作业在家完成,上课时带来,先由学生互相提意见,老师最后再点评,沿袭了当年“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传统。授课过程中, 雪涛先生曾经拿出祝枝山草书手卷,启发学生理解书法用笔在写意画中的作用。老师改画过程中,有时会指出学生题款上的问题,强调要写字,要做足基本功。当时使用的教材,是王雪涛先生的《写意花鸟讲义》。这时期,衲子由传统画家白纸对晴天时如何洒洒落落、幻化出一幅幅奇妙的图画过程中,悟出只有对生活的理解、默记功课做充分以后,才有可能“取象不惑”,才有用笔的稳、准、狠的道理;看到了中国写意画是如何用笔、用墨、用色、如何经营画面的,懂得了笔笔相生、阴阳相生、计白当黑、方圆共济、离方遁圆、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
1960年,雪涛先生在衲子新购的《任伯年画集》上题到:“艺术遗产中间可以继承的东西是不少的,但是继承的背后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工作,那就是革新与创作。列宁说过,保存遗产并不象档案保管委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鲁迅关于旧形式的采用意见是,旧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所谓采取是反对对遗产的粗暴态度,所谓删除是反对对遗产的保守态度,既有删除又有增益,就是推陈出新,达到古为今用之目的。”这篇指迷津要,与雪涛先生艺术上“不一般化”的追求,对衲子的艺术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由此深明取舍之道,衲子觉得雪涛先生作品中个人化的东西与己不合,只取了他的原理;而于汪慎生先生的简淡天真、洒脱不拘,在他心里却特别有位置。在两位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研读画史、画论、古典诗词。
同年,衲子考入北京工艺美校,这个学校的国画老师成就名气虽不如王、汪,但都是比较纯粹的中国传统画家,对衲子的影响也都是正面的; 也学习了素描和色彩,但没有动摇、改变他“中学为体”这个根本。1961年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常道先生,是出自“徐蒋体系”又比较早的否定这一体系的觉悟者,他总结出的关于中国人物画的一套创作手法,对衲子有较大影响。
衲子胸襟阔大,能转益多师,不死守一家门户。1980年代,衲子在位于友谊宾馆的文化部创作组,接触到众多传统老画家,开阔了眼界,收益也良多,其中对李苦禅、李可染借鉴之处最多,接受了黄永玉的写生观察方法,真正解决了关于形的问题。石涛曾说:”从耳根得来,又从而根失去。”纸上得来也未必不如此。所以他认为,只有手到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才能有比较鉴别,故此溯源林良、青藤、白阳、八大、石涛、周之冕、齐白石、吴昌硕等家,关注潘天寿、傅抱石,而对黄宾虹却更有兴趣。其中石涛作品的元气淋漓、生香活色,八大的冷逸、奇肆、凝重,齐白石的朴素、平静、视觉化特点,吴昌硕的浑朴苍茫、文化气氛和过人的功夫,他都有所借鉴吸收。衲子不拒斥外来艺术,对欧洲印象派之后的绘画有兴趣,更现代的只要是视觉语言清晰的、唯美的都在欣赏之列。
这期间听讲、观摩、请教,习作的点评、修改、研习、转益多师,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娴熟了技法,提高了水平,是为后来的发展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准备和积累。
当时年轻人受潮流的影响,都在忙着创新。本来就早熟的衲子,早已洞悉中国画的渊源流变及发展规律,更坚定了沿着中国自己的路走下去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嫁接西方。他也深明哲学、思想、文化对于绘画的重要性,还认为中国画的基本功、书法入画的笔墨、写意精神、诗情、意境乃中国画的命脉,是永远不能丢掉的。今天看来,这种认识是颇具历史眼光的。
3.造化心源
关于生活和造化,很多人的着力点在新题材、新内容上。衲子先生则更关注对象的本质和生香活色的感觉,造型上不采用写实的方法,是意象的、写意的方法,但这并不是说疏于观察、粗于观察。恰恰相反,他对对象的形、色、结构、生长规律、不同季节和风、晴、雨、露、朝、暮的变化,有着比写实派画家更高的要求。曾闻他曾对花卉做过解剖,以研究花的内在结构、花蕊是从哪里生出来的等等,格物致知到这种境界,在画坛怕是不多见的。而且,他在观察形、色、结构的同时,参悟的已经是用何笔法、墨法去表现的问题,甚至直接看到的就是笔墨了。通过全面深入的观察、体验、研究,将一切融化在心,最后他所表现的是全面综合、概括后的形象,超越了生活本身,所以更真实、更典型、更感人。
衲子先生也写生,必要时也借助相机,但他更有传统目识心记的功夫。他认同顾恺之“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的论断,强化自己独特的感受,有独见,方有独创。
衲子先生曾说:”写字画画并非只是书斋的事情,需得生活阅历,广以生活体验,悟得技巧。”青年时代农村生活的经历,培养了他与自然的感情,他的观察与生活在城里面的画家有所不同。他画《莲动知鱼子》慧心不啻在笔墨,画中莲蓬之杆以虚灵顿挫之笔写出,似有震颤感,款题:“莲动知鱼子”,提示观者这种“孤蓬自振”,是小鱼在水中触动的结果,给人以画外的联觉,与谢眺“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乃同一趣味,所不同者谢是诗之画境,此为画之诗境。
荷花是藕生植物,繁殖力很强,根、藕生到哪里,花叶就出在哪里,因此荷花常常呈现一线、一片、一堆的景象,这种盛夏花叶成堆成片错杂繁茂的意象,在国画是极难表现的,笔者以为历代成功的作品似不多见,而衲子先生《墨荷》、《水枕能令山俯仰》等一批作品,是这方面的创造,在画史上应有地位。衲子对荷花有长期深入细致的观察,画荷历经数变,以往这类作品常用石涛的方法,约略对苦禅先生也有借鉴,比比写来,且无一笔不可看。后来,他偶然在黄山看到石头上生出的片片的青苔,大大小小,深深浅浅,错错落落,很是奇特,从中受到启发,画荷风格又一大变,开出一种简练、概括、现代、深具内涵的大写意新风。悟对寻常生活,察人所不察,知人所不知,通其神理,移花接木,迁想妙得,得之造化,更得之于心源。
中国画外师造化,并不是主张如实地去刻画所见,而是还要传达所知、所感,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视觉艺术。衲子喜画鱼,儿时乡下河套那种野生环境里所见之鱼,与被喂养的鱼在习惯和灵性上有很大不同,其《安知鱼之乐》、《双鱼》等作品表现了他对鱼的独特个感受,加之其蒙养的笔墨和功力,对前人的作品是有所超越的,识者只要稍作比较自有鉴别;一千年来, 不断被文人阐释表现的四君子题材,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都是很难的,更别说发展了,衲子先生对此有所发展。他深研历代画家真迹,尤于郑板桥、石涛获益最多,又常年养兰,对兰花的生长规律、特点无不了如指掌,故每每笔头灵气即幻化为朝晨的清露,虽写兰在盆,却给人置身山野、芳谷的感觉,置之画史,毫无愧色。所画梅、竹、菊也无不如此。锋棱芒角总含情,才笔所到,皆情语,皆境语,非深究传统、书法入画、读书养气不能得之,所谓灵、情、才、化缺一不可。
4.通会圆融
如西哲所云:真学问、大艺术皆可以圆形象之。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衲子书法的功力,既已经变成本能,遂以此书法会通画法,故其山水、人物虽是偶作,也与花卉是同一笔墨,同一风格,同一水准;以此书法会通传统与造化、造化与心源、临摹与创作,故有创造之手眼。
画品之高,根于人品,画以人重,艺由道生。生活中衲子先生有口皆碑,传统人生哲学中儒家的“道德”、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的“自然”、守一、虚静、自得、逍遥,佛家的慈悲、清静、圆融,似乎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平素待人接物,平等、随缘、周全、中和、整体,已至圆融之境。以圆融平和的心态看待世间的一切,是一种品格,一种修养,它让人显赫时满盈若亏、不傲不狂,还可以让人安贫乐道,豁然大度。
大涤子尝说:“此道有彼时不合众意,而后世鉴赏不已者;有彼时轰雷震耳,而后世绝不问闻者,皆不逢解人耳。”衲子先生长期游离于学术界之外,不被批评家所关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少为世人所知,寂寞中不去迎合庸众的审美和世俗的政治,挺然于一切潮流宗派之外,陶然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仿佛豪杰之士,又仿佛空谷幽兰,令人钦佩、神往。
- 上一个藏品: 岭南画派艺术性不低价格仍然偏低
- 下一个藏品: 菜鸟抄底书画的简明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