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评高居翰《气势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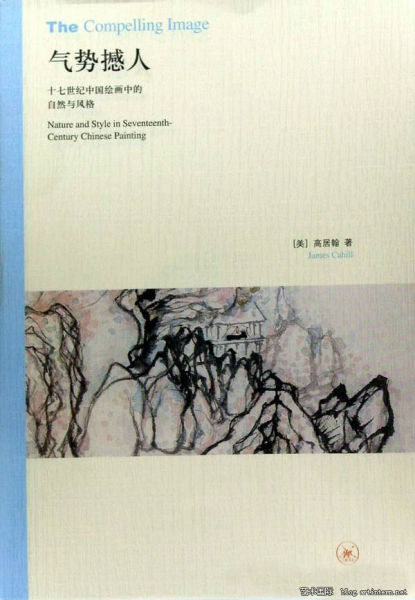 高居翰《气势撼人》
高居翰《气势撼人》
自1960年出版个人首部通俗读本《中国绘画》以来,高居翰就一直在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美国同行中居于翘楚的地位。他举办各种有启发性的展览,且因个人收藏与广闻博学而有重要的发现。在教学及各种学术讨论会上,他也颇受人瞩目。凭借他的学术成就,而被视为七卷本《中国绘画、主要画家及画论》作者喜龙仁先生(Osvald Siren)的得意门生,实在是受之无愧。高居翰不仅在其著作《中国古画索引》中出色地修订并更新了喜龙仁所出版的著作画目,更着手完成一套五卷本讨论晚期中国绘画的系列专论。[1] 1979年春,由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rlesEliot Norton)系列演讲为蓝本而出版的《气势撼人》一书,概略阐明了过去20年来高居翰在《中国画之玄想与放逸》(Fantastics and Eccentrics in Chinese Painting,1967)、《灵动山水》(The Restless Landscape,1971)、《吴彬与龚贤作品中的欧洲影响》(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works of Wu Pin and Kung Hsien, 1970)等著作中主要关心之所在,并且也集中展现了高居翰对晚期中国绘画中“自然”与“历史”的诠释。书后附有高居翰老师罗樾教授的评语,他以近似出版商的宣传口吻,褒扬此书是“西方研究中国画史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也曾获得美国大学艺术协会颁发的1984年全美最杰出的艺术史著作奖——查尔斯·莫里奖(TheCharles Rufus Morey Book Award)。
本人非常推崇高居翰的成就,然而,在阅读此书时,坦承不免有些隔膜。该书当然拥有许多卓越的品质——他用一种有趣且复杂的方式看待艺术作品,写作风格贴切自然,修辞技巧也非常高明;与此同时,也显示了他对西方艺术史、现代音乐、诗词方面的渊博知识,可谓才气纵横——不过,高居翰书中成果良莠不齐,许多说法也无法令人十分满意。本人不满之处,部分是由于我们之间不同的趣味、性情、背景以及学术训练等因素,部分则是出于对高居翰关于贡布里希“图像人”(image-men)和“词汇人”(word-men)所存差异之理解,我怀疑他书中的论述较注重词汇体系,倒是没有深入探究图像与思想的意义。
在书中,高居翰采用“一种文学或戏剧的结构”、“在忠实于自然和以传统形式建构的倾向之间……作明确的阴阳二元式的区分。”(参见该书序文)书中开始即以两幅绘画作品为例,以显示“写实自然与人为秩序的比照”:其中所谓“写实”的挂轴,为被人们所忽视的苏州职业画家张宏所作;另一幅依据传统形式创制的作品,乃是晚明宗师兼文人业余画家及理论家董其昌所作。由此而及,高居翰继而阐述“自然化与样式化此二种力量如何相生相成,……而产生出一批风格迥异的绘画”,因此导致了吴彬、陈洪绶、弘仁、龚贤、王原祁、石涛等六位17世纪重要画家的出现。
书中首页,高居翰转述了罗樾在《中国绘画之阶段与内容》一文中所阐明的观点。[2]依罗樾的说法,中国绘画艺术的再现时期大约结束于1279年南宋灭亡之际;元代以降的绘画则“变成了一种智性的和超再现的艺术”。作为一种评论概念,罗樾区分“再现的”和“超再现的”绘画,其观点类似于现代艺术批评中区分“再现的”和“非再现的”(或者说“抽象的”)艺术,此乃阿尔弗雷德·H·巴尔在1936年先锋派著作《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首先提出来的。[3]宋代以后的绘画发展可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相提并论,正如著名现代派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所言:“写实的或幻像的艺术都将媒介手段隐藏起来,用艺术掩盖了艺术,而现代主义作品则以艺术本身唤起了对艺术的注意。”[4]对于中国绘画“时代与内容”的变化,罗樾作了如下的定义:宋代绘画,其风格好比“一件工具,用以揭示或捕获现实的一件工具”,而在明清绘画中,“往昔风格开始当成主要的题材加以运用,且被视为本来的现实加以探讨。”
受罗樾说法之影响,高居翰也提出了对宋之后绘画的见解,他的著作屡次提及罗樾所称的“超再现的”或者“艺术史式的”艺术。[5]由于董其昌是晚明文人业余画家绘画理论的倡导者,故理所当然地成为“艺术史式艺术”的楷模。他认为“董其昌绘画中极度非自然主义式的作品,无论是在视觉印象上或是在形而上的抽象思索层面上,大多悖离了对感知世界的真实关注,其与外在的物质结构及其产生的自然现象之间,仅仅维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第37页);高居翰认为董其昌仅仅关心“借用风格以唤起与之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关注。”(第62页)
不同于晚明画坛“艺术史式艺术”主导的背景,高居翰在与董其昌同时但更年轻的苏州职业画家张宏的作品中,看到了以“再现物质世界真实面貌之画风”(第13页)。由于此画风表现出来的复杂面貌在罗樾简明的风格框架中无法得到处理,高居翰就此断论“促使其走向描写性自然主义新画风的诱因,……乃是与欧洲绘画的接触。”(第13页)接着他又宣称:“17世纪对北宋自然主义山水风格的重现,乃是中国艺术家突然置身于有相似特征的欧洲绘画中,……受之刺激而导致的结果,”(第76页),因此表现出“中国传统画科训练与外来刺激回应的一种趋同现象。”(第91页)
故而,此书的一个中心议题,便是论及欧洲绘画对于中国明清之际绘画可能存在的影响(第一、三、五章)。这是颇引人争议的。在此,有必要澄清一下我对这一议题的基本立场。本人并不怀疑西方绘画影响17世纪中国画家的可能性,关于这点,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对“南京画派”的卓越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沿此方向作更深入的探讨,[6]但我对高居翰以西方影响论,归结17世纪中国绘画发展之学说,依然有所怀疑。多年以来,高居翰一直宣称在吴彬和龚贤的作品中,有着极明显的欧洲影响。如今,他又致力于更广泛的文化考察,声称“在吴彬的绘画之中,以气势撼人的意象来营创出并不实际存在的世界,这种创作基调的灵感泉源,恐怕是得自于他的视觉经验所接触到欧洲宗教绘画的启发,在这些西洋作品中,艺术家为虚幻的事物赋予了实在的形体。”(第96页)高居翰进而归结出欧洲绘画使得中国艺术家“意识到拓展经验限制的可能性,包括在艺术创作中引发的想象过程,使其得以超越传统的禁锢。”(第103页)高居翰觉得“中国绘画对西方的反应态度,是与中国哲学及科学上的反应相一致的”(第91页),他将“中国晚期绘画中自然主义式的描绘不被重视的现实际遇,与同时期西方的科学知识、方法无法在中国生根的现象相提并论。”(第35页)
为了佐证这一论点,高居翰将晚明绘画中辽阔全景的构图与16世纪末像地图般描绘欧洲城镇的德国版画(如1572-1616年间在科隆出版的《世界城镇图集》(布朗与荷根伯格编撰)作类比,用以说明两者之间一些令人惊叹的视觉雷同之处。然而,根据苏立文的研究,这些欧洲地图版画是在1608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带到南昌的。[7]虽然高居翰也承认“有意识模仿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但在“观看一些欧洲版画时,遵循这种新模式来建构山水画的想法,却根植于中国艺术家的心中……新的意向和结构一旦进入到视觉记忆中,便会随意唤出,或者不由自主地涌现。”(第83页)对之,质疑者当然不会信服,因为高居翰据以为证的晚明辽阔全景山水,大体属于12或13世纪宋代绘画中“平远”构图之变化。我们在不少宋画作品中,也可找到与16世纪后期欧洲北部地图以对角斜线表示深度空间的相似画法。[8]
书中最精彩部分,是第四章“陈洪绶:现实人物肖像及其它”。秉承西方肖像画的研究方法,高居翰注意到“宋画中人物大半不向画外作正面凝视”(第114页),然后指出17世纪中国画中的人物“皆向画外直视观者,好似受到某种需求的驱使,而必须重申他们个人的存在价值,并隐约表白其存在的困境”(第124页)。“这种在画像与人物,个人与型式,真实与理想之间的交流,……是晚明绘画中的普遍现象。”(第141页)在高居翰看来,此现象显示了“晚明时期人的内在心性和外在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不和谐,完全阻绝了对中国传统理想模式中寻求现在与过去理想相辅相成之实践。”(第145页)。他在讨论陈洪绶复古风格时,让人费解地将五代变形风格画家贯休给疏漏了。如果以贯休为陈洪绶习摹的对象之一,则可借此探讨晚明及其他社会动荡时期,画家如何利用怪异风格来表达其心理状态。即便如此,高居翰对于陈洪绶艺术的见解依然是有说服力的,正如他在结语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作品弥漫着嘲讽的味道……反映了一种我们所熟知的讽喻,不仅意味着作品中高古人物的不可及,也显示着画家意识到这些典型是不能用正面且直接的方式加以呈现。”(第134页)这是高居翰最为高明之处。在我的印象中,尚无人能如此成功地勾画出晚明社会矛盾、冲突和衰败的图景,就像如实反映我们现实生活世界的一个镜像。
同样精彩的部分,是第五章关于清初画家弘仁由刻板的线性图案结构嬗变为柔静且不失壮美的画风描述,高居翰的形式分析,在此有着非常扎实稳固的基础。他以丁云鹏和萧云从创作的传统风格作品,以及凭借方志和墨谱而来的木刻版画之比较,一步步地展现弘仁“如何由线性图案形式以重构世界”。真是让人屏神静气,暗暗叫绝!倘若高居翰对龚贤作品也能如此解析,则必能摆脱龚贤画作乃是受到西方幻像表现手法影响之推论。在论及龚贤时,高居翰依然流于俗套,竟无视龚贤1680年代末期成熟时期的作品,而以现藏于苏黎士世里特堡博物馆的一件龚贤作品(约作于1670年)来诠释他称之为“自然变形”的最高潮。里特堡博物馆的龚贤作品,原无画家署款,后被人为添上。它的尺寸大小在17世纪的册页中,并非如高居翰所言的那么特殊,它原来是可对折的双面册页形式,其高度为62公分,比起王季迁收藏的董其昌一件高55×5公分的大册页,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董其昌另一件高70×2公分的“小中现大”册,并无特别之处。这张画的整个比例看来是极典型的横面册页,我们没有理由推论“这样的尺幅较接近西洋的形式,而不像中国传统的画幅”。(第178页)
在论及董其昌和石涛这两位关键性画家时,高居翰的分析尤令人失望。在此,我们不妨回到罗樾对中国绘画“阶段和内容”的描述,尽管罗樾对宋和宋之后绘画的动力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区分,但他却十分谨慎地声明“每一时期完全由内容而决定”,他本人则“不加任何历史风格的描述”。[9]将罗樾的观点付诸实践时,高居翰面临的难题便是如何描述晚明绘画的历史风格。
在描述张宏“自然写实风格”时,高居翰确信张宏“在绘画中减低风格的重要性,力使画面达到近乎透明感,此时画上的主题或内容,不受风格遮掩,可以直接观察到,就像宋代一些最好画作上可以见到的那样。”(第36页)这是对宋代或其它再现风格的极大误解。事实上,张宏新创的“无笔”风格(第22页),即便受到西方的启发,其对笔墨形式及格法和谐的追求,与董其昌并无二致,绝对不是没有遮掩的“透明”。正如夏皮洛(Meyer Schapiro)论及巴尔(Alfred Barr)的“再现艺术”时所揭示的:“在感官上不曾有被动的、‘照相式’的再现,……任何对于物像的描绘,无论看起来多精确,即便像照片,也无一例外都有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为基础。”[10]如果张宏笔下的自然形象“不是人文思想的投射……而是画家眼中见到的客观存在且自给自足的真实自然,”(第25页)那么,董其昌苛评张宏的画空洞无物,逢迎取巧,是“自然的奴隶”(第34页),也就无可厚非了。董其昌对张宏这类画家的批评,就像现代前卫画家对待杂志插图者的态度。
更严重的问题,乃是高居翰之于董其昌在理解上的隔膜。董其昌所显示出来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似非高居翰之解释框架所能把握。他将董其昌视为“抵制自然写实主义复兴的一种近乎道德势力的代表”,(第37页)高居翰只是含糊地将“精神与人文主义的价值”与“已确定的笔法惯例,形式类型及构图法则”相关联。(第35-36页)高居翰认为董其昌的“心智构成包含了一个由原则与价值观念所构成的恒久结构,尤有甚者,这一结构又与心智以外的世界相呼应”,(第64页)但高居翰并没有清楚地解释在“心智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有着怎样的等值关系,这种等值关系在董其昌绘画中的风格表现又是怎样?高居翰在评价董其昌“拙”的“逆转价值”时,又援引现代画家及收藏家王季迁的说法,称董其昌是一位“笨拙”的画家。(第60页)关于董其昌的笔墨,他也另加考量:“董其昌及其追随者坚持必须有好的笔墨,对他们而言,笔法不单单意味着一般所认为的技巧,遒劲有力或富于表情的笔墨,而是指某种特定类型的笔墨……换言之,笔墨不是有着明显的描绘功能……总的说来,笔墨可以视为儒家自我修养的视觉显现。”(第44、47页)但高居翰并未解释我们该如何由此主观价值判断切入,进而对董其昌作品建立一种“历史风格的描述”。
此外,高居翰对董其昌宣称自己作品乃融合了书和画、自然和艺术之论调,同样困惑不已。在他看来,“业余文人画家的笔墨,常被认为是其书法实践的延伸,这种说法尚待严格的限定”。高居翰认为“书法并不具备绘画中依照混合或重叠笔划以构筑物象形状的功能。”(第46页)他不无警示地指出,接纳董其昌言辞上的表面含义,是“中国艺术史研究最惯常的错误”。(第37页)特别是,董其昌本人宣称对“自然”和“风格”同样关心的说法,高居翰只将其视为董其昌一种未能实现的理论说辞,即“在理论上将许多他在绘画实践中所无法完美解决或无法漠视的矛盾,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这是董其昌解决矛盾的成功策略。”(第38页)高居翰在追寻绘画中自然面貌的平实表现时,埋怨“董其昌作品的结构完全背离了自然。张宏改造了他所继承的传统形式,使其适于描绘外在的自然形貌,董其昌则将这些传统形式进一步抽象化,以弱化形式的描写性。”(第53页)
但是,即便高居翰“图像人”能与“词汇人”亦步亦趋,我们仍然无法否认——中国晚期绘画的本质,诚如董其昌所代表的,乃在于书法与绘画、文字与图像、自然与艺术之间稳定不变的结合。中国书法与绘画,皆源于一个有意义的图像符号系统,其所要把握的,是自然的法则而非自然的形貌。中国艺术家的原创力,完全取决于“变革”固有形式与惯例的再生过程,或者取决于赋予艺术以生命的能力。再现即表现,8世纪画家张璪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1]这是中国艺术家信守不移的准则。中国艺术家从不仅仅限于再现自然的形象,也未曾发展出任何视觉再现的科学原理,因而也不需要“极端反叛幻象”[12],也无“非再现的”艺术。在中国绘画中,自然与艺术(或风格)总是密不可分的。
故而,与其将自然与艺术看成是相对或辩证的两面,高居翰还不如根据中国人“变”的观念,将阴阳区分的“自然化”和“样式化”看成是动态关联的、相承相合的一种力量和谐。这里所说的“变”,乃是宇宙万物最本质之存在。一旦高居翰如此处理问题,便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如他分析弘仁画作由线性图案形式转化为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样。倘若高居翰分析张宏、吴彬、龚贤作品,也能着眼于特定笔法、皴法、构图模式(正如龚贤遗留下来的那些画稿)的个人之“变”,包括可能的西方影响,我相信就不会有“于有意或无意之中赋予画面近似透明”的说法。
个人之“变”,是理解石涛的关键所在。他是晚期中国画家中最富独创性的一位。高居翰试图将石涛各时期不同风格与其居住地传统画风相关联,但我以为这是个错误的方向。高居翰以石涛1677年《东坡诗意图》(香港黄平常Huang Pin Chang藏品)册页为开端,将其中的渴笔皴法与弘仁的山水画相齐并论,试图证明“安徽画风影响石涛早期绘画的程度”。(第196页)然而,由汪世清1979年刊发的新证据显示,1651至1661年间,石涛在湖北武昌接受过早期的绘画训练,这要比他在1666年初访安徽早甚多。现存石涛最早的代表作品《十六罗汉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乃1667年石涛抵达安徽之后仅仅几个月所作,然则该画已显示出非常成熟的渴笔风格。再则,高居翰将石涛作于1685年著名的湿笔画风《万点恶墨》手卷,与石涛本人于南京时期以及龚贤的南京风格作品相比较。殊不知,石涛乃是在相同时期一起发展他的渴笔与湿笔风格。高居翰也将前属于樱木(Sakuragi)收藏的石涛1691年在北京时期所作几幅册页,与王原祈、王鉴的作品相比较。然则,樱木的这些册页属于非典型石涛画作,其真实性仍有待商榷,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也就颇有问题。
事实上,石涛早期的渴笔系统,同样是由启发弘仁的木刻版画插图衍生而来的;这些插画书籍,大多在安徽制作,成为晚明、清初年轻画家初学绘画最实用的工具书。石涛早年喜欢模仿的对象,也包括晚明印刷的唐诗插画集,这一题材对其一生有着极深的影响。虽然石涛渴笔勾画物象轮廓之法具有非常奇特的个性色彩,但他把线性技巧发展成一种有力的山水语汇,显示出可与弘仁和龚贤并驾齐驱的才能。而在石涛淋漓尽致的笔法——无论是线条、点法、大块点法——之“变”中,又存在原来单线笔法的不变逻辑,此即其后他所宣称的“一画”。石涛晚期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令高居翰觉得难以“按其先后时期及因果关系加以分析”(第211页),乃是由于其视觉上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皆与他居住的地方无涉,却与其一连串内在感应、自我和过去文化的记忆相关联,这些因素促使他急欲归返于某些主题和技法。石涛创作的秘诀,在于其个性化之“变”;这种“变”的方法,就是将无数资源及影响与一个他所称之为“我”的本体相联系。如果要了解石涛“变”之门径,惟一渠道乃是设法找出作品的来源、选择、思想、反应,以及这些因子与其创造想像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解释石涛的一幅作品时,高居翰犯下一个错误。这虽是小瑕疵,但却昭示:我们若想正确解读中国绘画,必须兼具一定的汉学素养。石涛的册页作品中,最富有情趣的,莫不过于那些借诗而作的图画,像王维(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苏轼(1036-1101)之诗文,悉是石涛取法的对象;这些值得深省回味的诗画,是画家藉由他们所倾慕的往昔作家的诗句来反省人生和自然。在诗文转衍为图像时,画家常常变化所引用的原文诗句,或者与古代诗人对谈,或者去反映画家自己的生活经验。在高居翰讨论的一幅作于1677年的册页上,道济节录了苏轼《四时冬词》的最后二行:“真态香生谁画得?玉奴纤手嗅梅花。”在处理苏轼所谓不可画之处,石涛一方面对诗画之间由来已久的的角逐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又婉转恭维了他的诗文偶像苏轼,并且也显示了他本人作为画家的自豪。但高居翰却错误地诠释了画面的意思,认为“石涛自己闻到了梅花的香味”,并将第一句诗文误读成“谁能画得出有生命植物的芳香?”(第198页)这使得此幅美丽图画的形象和内涵丧失殆尽。
如果我对高居翰的批评显得过于苛求,那是由于他书中不足之处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立场在我看来是成问题的。高居翰之所以过于夸大西方艺术对晚明绘画之影响,乃是由于他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他所采用的咄咄逼人的“分析新模式”(序文首页)及其对中国绘画史的全新观点,都有再次加以讨论的必要。高居翰甚至在董其昌作品中也看到西方的影响,他辩称“如果我们指认董其昌在其作品中使用了某些西方风格的元素,董其昌无疑也会找出一些中国画的先例加以反驳,尽管我们知道那完全就是一种遁词而已。”(第83页)由于高居翰将张宏的自然主义描写,等同于西方的实证主义手法,故他也把董其昌的“传统主义”与“晚期中国绘画因无法基于[张宏]的成就予以发展所遭受的损失”相提并论。(第26页)他断言董其昌标榜“对立面之彼此融合”,亦即董氏对“自然”与“艺术”同感兴趣的论说,只是与其创作实践不合的理论吊诡之观念(第36-38页),现代学者若把他的理论奉为圭皋,如果不是缺乏判断能力,就是太过于守旧。高居翰对于中国绘画史的全新观点,事实上反映了西方人一以贯之的陈旧态度,即将非西方的事物看成是泛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态度导致了所谓“中国艺术之研究”和“欧洲艺术之研究”的区别(第36页),从而滋生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之论调——将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牺牲了在超越文化藩篱之上、建立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贯通机会。
在其别的文章中,高居翰一直十分热衷于从社会、文化脉络来理解艺术的意义。他特别强调研究者要注意探讨赞助人,社会经济的乃至于地域性的区别。在《气势憾人》一书中,高居翰只是“简略地论及诸如画家生活环境这样重要的课题”,且“不太关心明清历史如何透露出有关绘画的资讯,相反,却要经由明清之际充满复杂变化的绘画,洞察那个时代知识界的压抑、以及对极度文化创伤的自我调适。”对艺术史研究者来说,艺术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棘手的难题,当我们努力去考论时代特色时,又当如何将董其昌和陈洪绶、王原祈和石涛的作品关联起来?从那些时代艺术与理论的反映来看,17世纪初期与后期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该如何连贯艺术家不同层面的创作生活?譬如石涛在诗与画的创作,应该如何处理?
艺术当然不可能脱离与所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但即便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也会承认艺术仍然多少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而非全然受到社会文化、政治脉络之操纵。[13]因此,一幅画视为反映某一特定社会或文化脉络之前,一定先得考察其技巧、形式和其传统习惯如何自行发展自此?将其视为一种视觉结构,而非单纯当成自然形貌的再现或“艺术史式的艺术”,此正如贡布里希(高居翰经常援引的作者)所论:“艺术有其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假使没有传统知识的帮助,自然山水无法经由未经艺术训练的人来充分表达。”[14]
高居翰“分析新模式”不愿意(或不能够)对风格作具体的描述。虽然他一再论及“意义结构”(序文首页)和“美学架构”(第37页),却从不尝试分析绘画中的形式关系与视像结构(形式的观看与结构方式),若能如此,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视像结构在历史上连续的演进历程。(他将京都小川广己氏收藏的传王维《江山雪霁图》手卷,与董其昌的《写王维诗意图》相比较,然而,不给任何理由,就声称小川氏这件藏品“是根据董其昌所见本再加以仿作的一个劣质本子。”(第47页)高居翰指小川氏藏品是作于董氏之后较晚的模本吗?为什么?作何解释?)
书中,高居翰认定张宏的创作观是“横向扩展,希望能够在直接经验之上,与同时代的人建立起一种共同的关联性”,而董其昌创作观像是“努力发掘一口井,但求其深不求其广”。(第59页)从理想上来说,我们却希望艺术家和艺术史家皆能既深且广。我个人的信念则是:致力于视像结构或绘画中“看法”的传统守成式的分析,仍是明晰领悟风格的有效途径。严谨有序的风格分析,必能获得对艺术史的通盘认知,而不致于产生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盲从的弊病。一旦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绘画中“变”的演进序列,一个“变”的模式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意义,也就自然地揭示出来。从宋代的图绘再现,到元代的书法式自我表现,再到明代的复古及清初的集大成[15],我们从中得见中国山水画史在各个时代的风格变迁。14世纪的中国画由图绘再现到书法式自我表现这一转变,正与20世纪西方现代绘画运动有相似之处。宋之后的中国绘画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对“往昔”的不同态度:对西方艺术家来说,现代抽象艺术最可怕的危途,不外乎是“放弃创造野心,回到陈腐的过去。”[16]相反,中国艺术家却总是把“复古”当作摆脱现实陈规陋习的手段。宋之后绘画求新求变的不二法门,即为复古和集大成。
书的最后,高居翰将王原祈与石涛视为在“有法”与“无法”两种途径间作最后的决战,至此,他将全书带入一个高潮。“[石涛]似乎为即将来临的一个伟大的绘画世纪奠定了基础,此时,传统的包袱终被摆脱,自然和艺术终于取得了协调。然而,其后的发展并非如此。”(第216页)他最后判定:“石涛凭一己之力,企图解放传统绘画的包袱的失败壮举,为这个时代划下了句号。”这是很适合本书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但我绝不相信石涛或者其他17世纪的中国画家,会像高居翰所说的“一个伟大的绘画世纪,此时,传统的包袱终被摆脱。”事实正好相反,经由模仿他们对自然(世界)和文化(过去)的内在反应,而非仅取其外形,王原祈和石涛皆成功地将外在世界及典范带回到他们的内在自我,终究完成了各自个别的集大成和“变”。
总体而言,高居翰此书依然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书中完整的结构体系,生动的历史想像,实在令人称道。我以上的评论,只是献给可能对反对意见感兴趣的一些专家,对于不是专门研究此学问的读者,特别是从事西方艺术史及汉学研究的同仁,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他们郑重推荐这部《气势撼人》。这是迄今为止论及17世纪中国绘画诸多论著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本。(黄厚明陈云海译)
- 上一个藏品: 吴山明执教50周年从艺60周年中国画展即将展出
- 下一个藏品: 擦亮眼睛看中国新水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