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与古籍善本相伴一生只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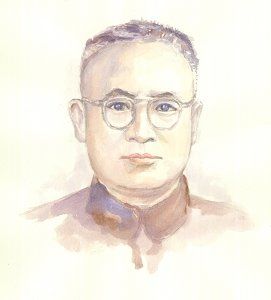 赵万里像 陆林汉绘
赵万里像 陆林汉绘
在赵万里(斐云)先生(1905-1980)不算太长的七十五年生命历程中,竟有五十二年的工作时光,与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相伴;而今收入洋洋三卷《赵万里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著述文字,也绝大部分与此相关,则其一生为书,可以想见。
当然,除了书,赵先生在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亦不乏可观:年方二十,便在大学临毕业前离校赴北平,拜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静安(国维)先生为师,并兼助教。1927年,静安先生辞世之后,又在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同时,陆续编成如今皆收入《文集》的《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遗著选跋》《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对后世研究王氏其人其学,功莫大焉。再由《文集》所收《斐云词录》《谈柳词》《词概》,以及《天宝遗事诸宫调校辑》《关汉卿史料新得》诸作,能知其倚声填词的创作水准和词曲研究之功力造诣。至于《文集》之外专书另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更是极具学术价值且影响及今的金石学经典名作,因而被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广西师范大学暨鸿宝斋(2008年)等一再翻印重版。此外,《文集》中《中国史料目录学讲义》《目录学十四讲纲目》《校勘学纲要》《版本学纲目》等赵氏当年在北大、清华授课的讲稿提纲,又可见其在文献学专业教学中独到的心得见解和视野方法。如“特重中国文学及文学史之新旧史料”的《目录学十四讲纲目》中,“目录学不限于线装书,凡一切地下材料及古代美术、艺术遗物皆属之” ,“古铜器中韵文铭识与《诗经》之关系” ,“汉石经、鲁诗与毛诗之异同” ,“石刻镜铭中之六朝文学史料” ,“唐人选唐诗略说” ,“旧本宋词编次法之特点” ,“宋刻宋词之分布区域” ,“毛晋父子保存旧本词集之特色” ,“明代别集总集中之短篇散文” ,“明清八股文学史料”等专论章节,无不堪称启迪思考、引人入胜之说。而其当年在课堂上的风采,则尚小明先生所著《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中,也有评述:
年轻教师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如赵万里,1929年8月到史学系任教的时候,只有24岁。他是一位版本目录学家,史学系的必修科“中国史料目录学”一直由他讲授,很受学生欢迎。
更多引当时亲历者所记:
赵先生是教“中国史料目录学”的,年纪在二十几至三十左右。蓬蓬勃勃的神气,严肃而带有刺激性的面孔,会教你见而生畏。每当讲书时,用一种紧急的声调,“烟士披里纯”的口吻,滔滔不绝的演述着。每一个同学,屏着气息,不敢说话,不敢笑,不敢斜视。侧耳静听,除写字的飕飕声外,一切都在沉默着……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夏岩《关于北大的两个青年教师》,《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18期,1935年1月14日)
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尽管有此种种,但对二十三岁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中文采访及善本考订组组长、并服务终身的赵万里先生来说,为图书馆访求、典守善本珍藏,或许才是其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真正所在;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宝贝”,他尽心尽力,甚至还有几乎不近情理之举。
抗日战争期间,蛰居沪上“孤岛”的郑振铎先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与张菊生(元济)、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张凤举诸先生,共同发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秘密收购古籍珍本,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故家旧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王伯祥、张葱玉、张耀翔夫妇、王馨迪夫妇等在沪友人的各种帮助;而北平方面,间道来沪的徐森玉先生和往返两地的赵万里先生,助力尤多。刘哲民、陈政文两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一书中,“致张寿镛(咏霓)”诸信所述有关种种,并“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辛苦” 、“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诸语,皆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振铎先生受命赴京,主管文化部文物局事。不久,赵万里先生也在原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后,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受文物局委派,他常常亲出访书,四处网罗珍本。而为将各家私藏谋归公库,千方百计之下,竟招舆情不满,怨声颇起。其间内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所刊柳向春先生整理的《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六十多通中,多直言不讳:“斐云在南方购书不少,且甚佳,其努力值得钦佩。惟心太狠,手太辣,老癖气不改,最容易得罪人。把光明正大的事,弄得鬼鬼祟祟的,实在不能再叫他出来买书了。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先生是能够原谅他的,否则,上海方面也会提出意见的。”虽责怪之中仍有赞赏,却也是实话实说。“老癖气”可能指赵氏平日一贯比较高调而言,民国间王佩诤先生撰《续补藏书纪事诗》(收入伦明等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其记陈乃乾、赵万里两位的一首中,即有“恂恂儒雅陈仲子,虎虎生气赵王孙”之喻,并于诗注中述陈氏“为人也和平中正,休休有容” ;而赵氏则“二十余年前来苏,主瞿庵师家。见其入门下马,行气如虹;头角崭新,睥睨一切”。“鬼鬼祟祟”似较形象,邓之诚先生在1950年1月29日日记中,也称赵氏“人极诡谲……今年以四千万人民券买铁琴铜剑楼之书十二箱以归公。欲买吴县潘氏滂喜斋之书,未果”(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4月)。而沈津先生《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950年1月6日条下,引顾氏日记曰:“赵万里来……并言常熟铁琴铜剑楼书成交,计购三百种,三千万元。赠四十二种。”至于“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云云,未明具体所指。今《文集》第一卷开首的编年体《赵万里先生传》(赵芳瑛、赵深编,胡拙整理)中,唯1950年及1951年12月两处,颇记赵氏受文化部委托,在同乡友人宋云彬先生陪同下,多次往访浙江海宁著名藏书楼蒋氏“西涧草堂” 、“衍芬草堂”后裔及族人,谋洽将其世代所藏,捐献国家并最终成事,而其中宋元精品,又拨归北图。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顾廷龙年谱》1951年12月21日条下,亦据顾氏日记,谓“瞿凤起女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则确是当年赵氏在沪上谋购铁琴铜剑楼藏书时发生的事情。
《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后,附有徐森玉先生1952年2月19日给儿子伯郊一信,其中提到“此间谢、刘均成贪污犯。赵斐云来信,渠被检举,甚严重”。可知此时赵氏已经遇到了比“怨声”更大的麻烦。差不多同时,郑振铎先生也有致徐森玉先生一信(原信仅署二月十六日,无年份。然信中有“回京已二十多天,以全力投于三反运动,未及奉函” ,“我们想不到谢某人竟会也是一只大老虎!人其可尽信乎”诸语,而当年“三反” 、“五反”运动的时间,主要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再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9月版郑重先生《谢稚柳系年录(增补本)》1952年下记:“《解放日报》于是年二月十九日发表了报道,题为上海文教部门打出十只‘大老虎’……在这篇报道中的‘十只老虎’,就有一只是‘字画老虎’谢稚柳。”则郑振铎先生所说“谢某人”,应指谢稚柳先生。故此信亦当写于1952年初),在写完后未寄出之前(二月十八日),特地“又启” :“又我局去岁曾向瞿氏铁琴铜剑楼购善本两批,计共两亿元。请先生代向瞿氏兄弟一询:有没有人向他们要过钱?他们给过没有?有没有给过人什么‘书’(包括赵斐云及文物处的几个人在内)?请他们据实答复(不可代为隐瞒)为荷。”再由郑氏信中说赵氏“近来精神至为不振,交代问题不少。闻曾函先生,语多悲戚”等等,则其当时处境,可想而知。不过,郑氏还是坚持认为:“他毛病很多,但确是一个人才。群众对他也还不至于压力太大,在他已经是接受不了。经过这次运动,他过去的一切身上的污垢,当可完全洗清,成为一个‘新人’了。”果然,到了七月二十一日的信(因信中提及上海图书馆将于二十二日开幕)中:“斐云问题已解决,只是记过。但他思想上仍不易搞通。昨晨谈了半天,我已切实的规劝了他一番。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把善本书目续编编好。限他半年工夫做好这个工作,诸事不问,也不必再管买书的事。他已经答应了。”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能如此了结,恐怕已属不易;而郑氏爱惜人才,亦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当年郑振铎先生自己为公家搜集包括书画图籍在内的各类文物,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致徐森玉先生的那些信中,不是挖掘人脉关系以助追踪征集,甚至详列“非要不可”的名品,便是安排如何具体操作以达目标,包括商讨谈判细节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辈爱书如命,求书如渴。为人民得善本名画,即大费心力,亦将乐此不疲。”因此,对赵万里先生其人其事,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有着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的爱惜和理解之情。而那种强调文物应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当入公库保存的观点,则不仅是他们的共识,也是一种很有时代烙印的历史存在。文物古玩界前辈马宝山先生,曾在其《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的《李衎〈四清图〉的风波》一文中,专记解放初因谣传由故宫散出的“东北货”元代名家李衎《四清图》卷在其手中,有关方面便让其“赶快交出” ,弄得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直到友人告诉他:“《四清图》已有下落,惠孝同听说你蒙冤,他就把《四清图》送到团城文物处去了”,这才“如释重负”,并敢去团城见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命我把所有的“东北货”和早存珍贵书画,全部开列清单,送文物处审批,而《四清图》的事,竟一字未提。
在这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结束业务,回老家去种地。所以赶快选了所存珍品二十多件,最名贵的是顾恺之的《洛神图》(即《国宝荟萃》刊印的那件),还有唐孙过庭书《景福殿赋》等等。这些珍品共写了二千七百余元,开了清单送到团城。徐邦达、张珩二位看后说:“你写的这价对吗?”(意为定价太低)我连忙说:“对!对!”
不久,“三反” 、“五反”运动起,罚了我店二千八百多元。古人云“云烟过眼” ,这句话我深有感焉。
至于熟识的朋友之间,更是直截了当。黄裳先生就在怀念郑振铎先生的《拟书话——〈西行书简〉》(收入氏著《珠还记幸(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中,有这样的回忆:
又一次,我在来青阁买到一册宋本的《尚书图》,是南宋建阳刻本,白纸初印,有胡心耘跋,在古版画中算得是最早期的作品。西谛收古版画数十年,著有版画史图录,不能不给他看看,于是再访团城。西谛一见此书,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急问在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不容分说,就做主留下,照原价由国家收购,马上送到正在举行的雕版印刷展览会上去了。
需要顺便一记的是:笔者昔日曾当面问过黄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还将另一珍稀稿本《远山堂曲品》捐入北京图书馆,是否也是郑振铎先生的意思?回答为“不是” 。谢国桢先生在《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收入氏著《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一文中的记述则为:
一九五八年我从南开调到北京科研机关从事研究工作,与君和向达(觉明)先生来往尤密。我是喜欢收藏书籍的人……偶然遇到两三种善本,如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以及南宋袖珍刻本《宋名臣言行录》,斐云兄说:“这些书非归北京图书馆不可。”我只得把它们献给公家了。
自然,也有“不买账”的事。郑重先生在“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文物出版社2007年3月)一书中,记1962年赵万里先生来沪,到文管会拜访前辈徐森玉先生,谈起流落在外的宋龙舒郡斋刻本《王文公文集》残帙的收购事宜,赵氏提出: “《王文公文集》要拿到北京去。徐森老,你一直是北京图书馆的保护神,这件东西一定要给北京图书馆。”没想到,“听了这话,徐森玉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放屁,你只知道什么都弄到北京去。做梦,绝对不行。’谢稚柳在旁边打圆场,说:‘八字还没一撇,你们闹什么。森老,你坐下来。’徐森玉坐下来,赵万里跑到徐森玉身边,也坐下来,用手摸摸徐森玉的光头,说:‘平平气,平平气,以后再谈。’徐森玉说:‘没什么好谈的!’”对赵氏这种“什么都要弄到北京去”的做法,黄裳先生也很不以为然。《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所收明万历本《利器解》一书的跋语中,就特别提到:“赵斐云南来,闻石麒告以此书端末。大呼如此好书,何不归伊。倩石麒向余索观,余则靳而不与。非秘惜此书,实厌其为人耳。”但对其学识水平,则十分认可:
十年前海宁赵万里来斋中观书,示以此册及李因竹笑轩吟草三集。斐云欢喜赞叹,出小册录行款序跋而去,而于他旧刻不如是之重也。斐云知书,更好诗余。湘蘋青玉案满江红诸调,都能默诵。得此真赏,亦足快心。(清顺治本《拙政园诗余》跋)
此书买得后,即付重装,未遑考索,亦不知其名,但知为明初旧本而已。今日赵斐云来斋中观书,示以此册,欢喜赞叹,以为未曾得有,盖即洪武原刊之《太和正音谱》也。(明洪武本《太和正音谱》跋)
1980年5月,赵万里先生去世。三十年前(庚寅,1950年)曾因不满赵氏某些行事而“实厌其为人”的黄裳先生,以“黄垆之痛”的悲情,在他那本劫后幸存的《太和正音谱》上,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斐云久病,余念之不已。实以近时版本之学,无逾此君者,人才难得也。半月前余以事入京,晤谢刚主,告文化大革命中斐云所遇诸酷。先是为拘系于地下室甚久,阴湿不堪。逻者知其性最畏蛇,乃以置于卧具中,大惊怖,遂中风,以至不起。近国家订定全国善本书目,聘顾问三人,周叔弢丈外,斐云亦其一……斐云得讯大兴奋,终夜不能眠。翌日疾作,遂卒。余访北京图书馆日,适为斐云送葬之辰,因得一赴,并睹遗容,不可谓非有前缘也。此本余初不知为何书,斐云一见,即断之为正音谱,检视果然。此种眼力学养,今无之矣。
- 上一个藏品: 古旧医书能否迎来藏市春天
- 下一个藏品: 古籍收藏:首先要真正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