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乔斯:生于乌托邦死于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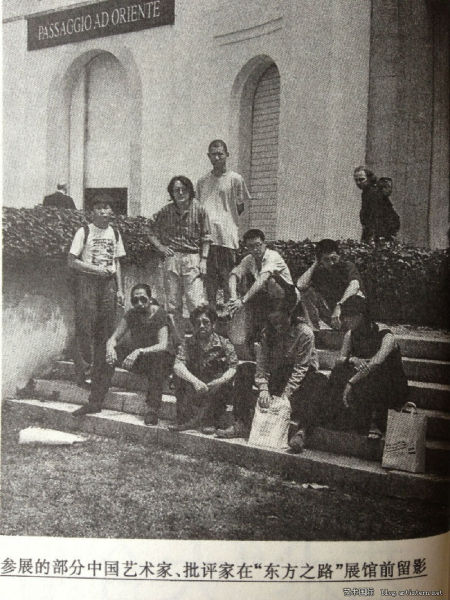 图片资料
图片资料
 2009年6月吕澎、张晓刚、周春芽、王广义在威尼斯
2009年6月吕澎、张晓刚、周春芽、王广义在威尼斯
翻开《江苏画刊》1993年第11期是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特辑,《来自威尼斯的“大合唱”》:“一群中国人到威尼斯‘旅行’
中国当代艺术家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这是一个在本世纪历史最久、最为世界艺坛瞩目的展览,这是一个不仅见证了整个二十世纪艺术史,而且也对当代艺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展览。这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中国艺术史及双年展百年史因此记录下一个新的艺术事件,并留下以下的名字:栗宪庭、王广义、徐冰、方力钧、刘炜、喻红[微博]、冯梦波、张培力、耿建翌、余友涵、丁乙、孙良、王子卫、李山、宋海东、孔长安、王友身、吴山专、李铭盛、陈箴。”
如今已经很难揣测他们当年奔赴威尼斯的心情,如果把故事放回从八十年代走来的过场。八十年代的遗憾是梦想是很多人的而不是个人的,集体做梦与集体不做梦的生命底色是不一样的然而如今也无关紧要——如果一个时代在未被通知前就被彻底背叛了,那么对于任何个人所受的残忍都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命运总是始料不及的。那时圆明园画家村生命力正蓬勃,89现代大展的伤痛背后,处于本能,艺术工作者开始寻找新的展览方式及可能。与其说中国的实验艺术在这个时候被香港、台湾和西方的策展人所“发现”,倒不如说是最后一次集体的梦想即将散尽前的回光返照刺痛了旁观者的眼,时势造英雄。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将中国实验艺术推向国际的张颂仁,还是将中国摇滚乐带出国境的张培仁,他们的选择本身就是神话。经历过90年代人们会认为,那是一个“很干净、孤独的、尖端状态”(张小涛语),就像在94年的红磡体育馆,中国摇滚新势力的那场划时代的演出上,弹出的每一个掷地有声的音符都是态度。何勇戴着红领巾穿着海魂衫在英国殖民地呼喊:“你们吃了吗?”后殖民的泡沫就不攻自破。那是20世纪最后的浪漫,无需现实,只要自由,人和人的差距就是明天早晨谁生火做饭,是吃油条还是饼干。所以我理解的“历史之路: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20年”特邀展的诞生,只是在时间线上的一次全面回顾。一种充满人情气息的形式,一种邀约,一个承诺。20年世事变迁,20年世态炎凉,20年恩恩怨怨,感激谁怨恨谁,谁向谁say sorry,谁又在忏悔。20年前的奥利瓦雄姿英发,20年前的吕澎[微博]还在商海挣扎,如今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硕果累累,每一个心灵的背后都是来路曲折,唯有后人揣测。
时隔20年,自由在萎缩,精神在萎缩,态度在萎缩。伴随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拉开的帷幕,没有了当年划时代的意义与心灵严肃的震撼,络绎不绝映入眼帘的,是三教九流艺术家们对于“威尼斯神话”的狂热追捧以及似是而非的策展人经销商似的包装与操作。条件自然是艺术家镀了金子,留下作品,日后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谁都不愿意相信自己踩的是香蕉皮,狠摔一个狗啃泥。幻想就像是原弓的《空香6000立方》,处处散发着中国茶叶腐朽的气息,这种无耻是中国式的狂热,是缺乏价值判定的无信仰国度的又一次人心暴乱。去年一个捕风捉影的核辐射就能引起大范围的盐荒,可见国民的愚昧较之鲁迅时代追求一块人血馒头的执拗有增无减。如今“威尼斯”就好比那块人血馒头,哪怕凑过去闻一闻,也能百病全无,返老还童。把舞台造到观众面前去!把拍卖数字推到天上去!不顾一切,谁还在乎理想与自由?
即便有人赞助了萨子50万,让他走完从威尼斯归国的旅程,也并不能说明艺术机制的完善,也不意味着艺术家高枕无忧。时代的改变川流不息,在“未曾呈现的声音”开幕式上,我看到了90年代总经理式的衣着,伴随着90年代流行的最为粗糙的行为艺术语言,随处可见的下体,自大的内心,引来国内外骂声一片,于是了然:这就是“未曾呈现的声音”。其实没有什么是“未曾呈现”过的,他人已做,并且比你做得更好。历史只需要一个代表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之于人类史的意义是第二个吃螃蟹的人无法替代的。如果艺术家还有勇气承认艺术是精神的追求,那么请相信,它不在威尼斯。
一种背离本质的价值判定体系的约束力从来没有削弱,这是导致自由在不断萎缩的原因。任何传统悠久的文化盛事必有其流传的精神要义。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更高、更快、更强”,推崇的是人类个体的极限与毅力与信念互筑而成的奇迹。而在国家导向里却变成了一块金牌榜,站得越久,说明我们把虚荣看得越重,越想赢得尊重,越是诟病百出。人性普世的弱点犹如坑洼,从来都不是依靠高尚的道德和理智就能将其夷为平地的。交钱办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故事背后是两全其美各取所需。威尼斯双年展诞生于1894年,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之初,创造一个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盛事这不失为一种民族主义策略,就像美国的文化野心在于让波普艺术占领全球,让人们一看到可口可乐就想到美国;让科幻电影占领全球,基于美国的科技基础以及“高边疆”太空战略的作战重点,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树立一个最具创新精神的文化样本,而这种带有政治导向性的文化输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启迪了一代人的世界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带着批发的“当代艺术”去威尼斯,到底作甚?
肯尼亚馆里横空出世“再中国”,王春辰[微博]的“变位”就是一剂谶语,胡曜麟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自作多情,孤立语境,就算把天安门城楼搬去威尼斯也照样是文不对题词不达意。不论如何,艺术家们都在以宗教般空洞的热情努力配合着在精神关照消解的时代里追求“变位”后的全面“变味”。对于威尼斯,这个一半是神话,一半是陷阱的城市,还有没有人愿意为了守护理想中的美而在瘟疫肆虐的之际不忍离去,安详地长眠于此,从而心生宁静。
20年前,吕澎撰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仍然热爱艺术吗》,是如此的接近乌托邦。当时它不够强大,却依然纯洁。它没有在电视报纸上欺骗过你;它也没有把谎言当成真理告诉你。因为它始终坚信:我们的心灵,是由纯正的精神力量构筑而成的,良知的堡垒。
“我们应该仍然热爱艺术,因为艺术仍然在为我们提供幻想、想象的空间,提供探索漫无边际的精神领域的乐趣。艺术仍然在改变我们枯燥的工作与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它就像一种润滑剂使得我们的大脑这台机器不至于锈蚀。它仍然在提醒着我们,生活的可能性还没有穷尽。”
对于无知,幻想是一种进步;对于良知,放弃是一种罪恶。以此作为对于理想时代的总结,抑或告别。(完)
注:《死于威尼斯》是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代表作。故事讲述生活紧张严肃的且事业处于巅峰作家阿申巴赫在一股强烈的旅行热望的驱使下来到威尼斯,在饭店邂逅波兰少年塔齐奥并对其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爱恋”,在瘟疫侵袭时仍不忍离去最终孤独而满足地死在荒凉的海滩上。而少年站在海边,面对浑然不知的爱恋,将手指向了天,仿佛是死亡的另一种延续。
- 上一个藏品: 对话展洲国际开园展策展人黄梅
- 下一个藏品: 杜尚的小便器:启蒙现代性的逻辑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