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丛生的当代艺术小气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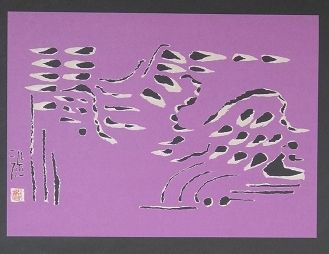 张杰《气候系列1》
张杰《气候系列1》
徐佳和 采访整理
自2011年开始的“江汉繁星计划”是武汉美术馆对于青年艺术家的推动项目,本届主题为“气候”,从自身的角度展现气候与人的关系。展览同期举行了青年批评家研讨会,会上,来自各地的批评家对于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文化“大气候”和个体经验“小气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当代艺术偏向于大,在这样一个大的尺度下进入对于小的关注,关注小是什么样子,是 一个好问题。在今天的所有展览系统来看,艺术作品的尺度确实是越来越大了,经常甚至是十米高的,几百米、上千米的大空间去放一件作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入这样一个空间的时候,看到那个巨大无比的,所谓的当代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看的速度会超级快,甚至像走路一样的,从展厅的这个门进去,马上走出来了。好像是看明白了,但很难在那里面更深入地停留和观看,这是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最近我在看周思聪晚年荷花作品时特别有感触,一张画的尺寸基本上是四尺对开以内,我去看一张画可以看上一二十分钟甚至有想流泪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很少有观看一个平面作品或者是当代艺术作品会流眼泪了,我们可能听一首歌会听得流泪,但是看一个作品很难。那么面对尺度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深入?这样文化资源共享的方式本身可能也面临一个问题:有些东西的生成不太适合共享,如中国的手卷或者册页。从作品生成到最后被观赏的完整生态里面是被三五个人相对封闭地体验了,当这样的作品现在进入一个大的美术馆空间的时候,挂在墙上的时候它被消化掉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我们也准备尝试一种长期性质的预约机制,来保证项目的参与、沟通,反大众传媒逻辑,用这种方式使传播更有效,促使系统再生成性,或者是蝴蝶效应,二次传播的自我建构的逻辑是不是能更有效。
张新英(《中国版画》执行副主编):最近这几年当代艺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追求形式震撼的作品少了,追求耐看趣味的作品多了,吓人的东西少了,精致的东西多了。除了材料的考究以外,制作上、各种各样创新的方法、数字化手段的介入都有让观众参与其中的乐趣。有一些批评家认为这说明当代艺术丧失了自己的先锋性,迎合了观众的趣味,但是我更愿意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艺术家自我观念系统完善的一种努力。因为今天的各种信息都是碎片化的,诱惑也多,压力也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把这比喻成德国哲学家集歇尔的“游戏反应论”,人们在这样一个幻想丛生的环境里面其实是会被逼疯的,2008年英国怪女孩萨拉·卢卡斯的恋人菲尔赫斯特就选择了自杀,他觉得自己已经落伍了,跟不上这个飞速变换的时代,所以他就选择了自杀。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一个同期的同质的环境。在当代艺术的很多艺术家那里手工劳动是近乎于一种修行,就是在这种大量的手工劳作的过程当中艺术家在不断自我否定,追求人性完美的挣扎当中它才排除掉了外界的干扰,保证了主体自我的独立性。另外,我觉得精致趣味的追求和艺术效率的追求是有关系的,在追求效率这一点上,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发展策略是不一样的,现代艺术是以一种让你难以接受的形式强迫你去接受,进而达到一定的改变。当代艺术更倾向于以一种容易接受的方式达到一种改变,其实这等于是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艺术家把他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了,并且以一种实用的理念得到公众的接受。
卢缓(中华艺术宫学术部副主任、策展人):当代艺术更广义地说,不仅仅是视觉本身到底有多少边界的话题,我想今天我们在美术馆中做展览可能和在其他的空间会不一样,曾经我们对美术馆的认识,更多的是回溯、研究、总结,今天我们站在美术馆中,大家更多期待的是有新的发现。我们也会渐渐地把美术馆作为一个试验性的场所,尤其是对于年轻人的课题,他会在这里阐述不同以往的或者是在一些商业空间中无法实现的作品。作为美术馆的策展人,我越来越希望无论是做老一代的艺术家,甚至历史性的课题,还是今天我们做当代的话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基于研究基础,把一个展览从给观众创造一种图像的方式转向到去创造一个视觉世界。有句话说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但是我认为并非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在当下现实考虑之下,将这种技术对于生活的介入和改造作为一个具体情境而存在。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来关注年轻人的课题,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或者去介入他们的一种生活模式,而不是从我们自己个体经验出发,尽管我们也是年轻人,但不是从年轻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中去进行考察,这也许是我们未来发展有意义的视角。
鲁明军(四川大学教师、历史学博士):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古典绘画与气候关系的历史面貌,今天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把气候当做一个观看的对象和描绘的题材,可能我们对于气候的感知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艺术实践。根据我看的图片可能已经暗示我们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视觉,甚至包括嗅觉。而此时这种个体自身或者是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中可能保证身体的感官经验、理性的知识以及我们对于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的个人的回应。艺术从来不是自独的封闭的形式,或者是一种神秘的系统,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品既是对艺术史的一种否定性回应,也是它对所处时代和认知秩序的批判性的建构。我其实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历史学家对于气候的历史的重新解释,包括孟德斯鸠对于气候与政体的思考,以及这些艺术史家关于自然的讨论。艺术家们对于气候的感知和艺术实践,他们在各自的时代提供或者共享了一种什么样的认知方式,一种对于现实世界什么样的理解和态度,而这种认知方式以及现实态度对于历史和艺术史又是作出了什么样的回应?也许气候会成为超越简单的社会参与性和说教的现实感的关系美学和其不确定性的可能,因为前后有一个强大的感官系统和文化政治系统,气候恰恰是融合了这两个大的系统,这是有别于僵硬粗暴的政治艺术和去感官性的知识性艺术实践的最重要特征——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理论假设和期待。■
- 上一个藏品: Kantor正式担任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艺聚空间策展人
- 下一个藏品: 至上主义的奠基人马列维奇回顾展登陆英国泰特
